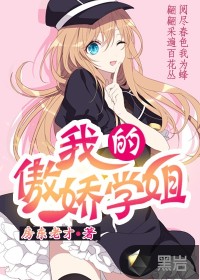忽而一只有力的大手伸了过来,用胳膊生生地扛住了大树,那人“人面不知何处去”,只见密密麻麻的络腮胡,肩上扛着一个书生,身边跟着一个小泥人。
“发什么呆,快爬起来!”钟若瑜喝道,胳膊微微发颤,疼得龇牙咧嘴。
渔舟在地上一滚,一骨碌爬起,伸手使劲将宣竹拖了出来,相互搀扶着颤巍巍地站起。
回望过处,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谈什么劫后余生还为时尚早,钟若瑜扔下大树,用受伤的手捞起宣竹放到了另一边肩膀上,解下腰带绑在渔舟胳膊上,五人磕磕绊绊地往东逃,手脚并用,翻山越岭。
直到申时末,双脚才沾到平稳的土地,虽然时不时地还会抖动一阵子,终于不见山崩地裂了,令人稍稍心安。
劫后余生的五人面面相看,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半山腰的草地上,如一条条晒干的咸鱼,一动不动地,皱巴巴的。
头、脖子、肩膀、胳膊、腰背、臀 部、大腿、脚无一不痛,头发、脸、衣裳、饰物、鞋袜无一不狼狈,但是众人暂且都顾不上这些,只想喝几口水,好好睡上一觉。
五人中数钟若瑜情况好些,虽有几分狼狈,但至少不会如另外四人般衣衫褴褛,这拾柴烧火、寻觅食物的重担自然也就落到了他肩上。望着身姿矫健的钟若瑜,这时候若还有人敢说他是个纯粹的商人,渔舟保证不打死他,而是要咬死他。再说了,褚进这个一州太守竟然会跟一个地位低下的商贾交情匪浅,渔舟是打死也不信的。不过是他们既然都未明说,彼此便聪明地装糊涂罢了。
渔舟的面前突然多了一个脑袋挡住了她望向钟若瑜背影的目光,有人轻声问道:“你不累麽?这水囊里还有一点水,你喝点吧。”
随之,她手中多了一个泥泞的水囊。跑了这么久,宣竹手中还拿着此物,也真是难为他了。
渔舟舔了舔干裂的唇角,拔开塞子喝了一口,还给了他。宣竹自己也喝了一口,又递给了灰头土脸的褚进。
渔舟按了按额角,苦笑道:“不是不累,也不是不想睡,而是只要一闭上眼,那种天摇地动的感觉就冒出来了,实在是晃得晕。”
“这次,又多亏你了。”宣竹握着她的手柔声道,情愫染上眉梢,眸光潋滟。
渔舟拍了拍他的手背,欲将手从他掌中挣脱,轻笑道:“别瞎说,救命恩人去觅食了。”
宣竹抓紧了掌中的小手,一点点地抚过她掌心与指腹上的茧子,微微叹了口气,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眸光低垂,掩去了其中的深色与情愫。
她总是这样,明明近在眼前,却仿佛远在天边,她的心思就像漂浮在天边的云朵,无论如何地去追寻,总是徒劳。
宣竹忽然觉得除了累,还有些冷,从骨子里透出的冷,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身子对温暖的渴求是那样地强烈,情不自禁 地向渔舟的身边倚了过去,可是靠着她觉得还是不够,将脑袋枕在她肚子上,手揽着她的腰,这才感受到了些许温暖。
若是从前的竹先生断然是做不出如此失仪之举,渔舟生死之际的那一扑让他再也难以压抑自己渴望亲近她的心。
“你这是怎么了?”渔舟伸手向他额头探去,并未感觉到烫人。
“小舟,我冷。”他含糊地应了一声,将整张脸埋入了她怀中。
渔舟无力挣扎,将手插 入他的墨发中,轻轻地梳着,不一会儿怀中的人便睡着了。
旁边一直在挺尸的某人这时倒似活了过来,似嘲非嘲地道:“你何德何能得他如此眷恋,如此情深?”
在褚进的眼中,跌入尘埃的竹大少依然是竹大少,与市侩的村姑始终是云泥之别,这种门第之见早已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
渔舟似笑非笑地道:“我对褚大人也情深得很,不然您的坟头草明年大概会有三尺高了。敢问褚大人又何德何能值得我相救?对了,都说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您是以身相许,还是当牛做马呢?”
打嘴仗褚进又怎会是渔舟的对手,只能冷哼一声,背过身子去生闷气。
“褚大人也不必腹诽,再过些日子,您这四品官兴许未必会有我这斗升小民过得自在。有些人啊,只有在绝境中才能看清自己的浅薄与愚蠢。”渔舟不痛不痒地道,“太守大人,您看同样是草地,您屁股底下那片没比我这片高贵吧?”
泥人小寒轻笑出声,褚进吐出了两个字:“粗俗!”
拎着野鸡回来的钟若瑜笑道:“看来,是我来晚了。不过,看到你们如此生龙活虎,我就放心了。”
渔舟垂目往山下望去,满目疮痍,山河失色,男女老幼横七竖八地躺着,哭声隐隐,炊烟少见,偶见行走人影,俱是衣衫褴褛,伤痕累累。此情此景,再无半分谈话兴致。
忽见主仆五人提着包袱向半山腰而疾步而来,虽是狼狈,然衣裳华贵,举手投足间不失优雅,显然出自大户人家。
渔舟以为是寻褚进或是钟若瑜而来,远远看了几眼便阖目假寐了。未曾料到,来者朝众人团团一礼后,急问竹夫人是哪位。
渔舟从未以宣竹夫人自居,首次听到“竹夫人”的称谓自然是陌生得很,直到钟若瑜轻笑出声,她才惊诧地回神,轻手轻脚地放下宣竹,起身敛容回礼。
看着眼前这个三十多岁的华服男子,渔舟并未掩去脸上的困惑。
“小舟,这位是知味坊的当家刘盛龙刘掌柜。”钟若瑜在一旁笑呵呵地道,显然二人相识。
“敢问刘掌柜有何贵干?”渔舟淡淡地问道。
刘盛龙满脸喜色,纳头便拜:“总算见到恩公了,多谢恩公救命之恩!”
渔舟侧身避开,忙道:“您先起来吧,在下与您素昧平生,这救命之恩从何说起?您该不会是认错人了吧?”
“在下唐突,惊扰了恩公,实在是对不住。”刘盛龙顺势起了身,笑道,“天灾忽降,大伙儿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沿途听到有人高呼须往东才能逃命,小的将信将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带着家眷往东跑,没成想还真的逃过一劫。方才一打听,方知这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出自桃花村的竹夫人,因而特来拜会!”
“这个可不敢当,大伙儿能够死里逃生,不过是土地神的庇护和各自的福报罢了。”渔舟浅笑道。
“恩公谦虚了。”刘盛龙温和地笑笑,心中不信她这番说辞,但是倒也未多言,转而言道,“这些是一些吃食和衣物,夜里寒凉,恩公一定用得上,请务必收下!”
“如此,倒是多谢刘掌柜了。”
这些都是急需之物,渔舟倒也未推脱。
刘盛龙再次郑重地朝渔舟行了礼,又与钟若瑜寒暄了几句,这才带着仆从离开。
“这人,倒是有几分意思。”渔舟望着他的背影轻笑道。
此番逃过一劫者不再少数,身为商人,即便素未谋面,却知恩图报,难能可贵。
“刘盛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知味坊不仅在宣阳城生意极好,江南、川蜀、燕京也是颇有几分名气的,他自然是不容小觑。”钟若瑜笑道。
野鸡再加上糕点,五人的晚膳倒不算寒碜。
不得不说刘盛龙想得极为周到,包袱中竟然还有一口小锅,这可极大地方便了渔舟和宣竹。皮糙肉厚的钟若瑜,身高八尺的褚进和精力充沛的小寒自然也寻了一处溪水,草草洗漱,换了干净衣裳。
夜阑人静,玉 兔东升,星河灿烂,忽而见彗星袭月,继而陨星如雨。
彗星袭月,白虹贯日皆为大凶之兆。
围着火堆的人们叩首而拜,五体投地,哭声震天,如丧考妣。
唯渔舟一人神情怡然自若,抖着二郎腿观漫天星雨目不转睛,神色欣然。
宣竹最先发现她的不同,倚着她问低道:“这难道不是凶兆麽?”
渔舟笑而不语。
宣竹不依,握住她的手,轻轻咬了一口以示惩戒。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倘若真是凶兆,难道拜过之后就能变为吉兆麽?如果不能,那又何必拜?”渔舟轻笑道,“对了,不是有句话叫天意难测麽?与其劳心劳力地揣测玄之又玄的天意,不如想明日吃啥更靠谱些。”
钟若瑜抚掌而笑,赞叹不已。
宣竹神色复杂,羞愧与骄傲交织。
褚进若有所思,对渔舟刮目相看。
夜凉如水,更深露重,心力交瘁的人们相继入睡。
渔舟神色恹恹地拥着大衣辗转反侧,不知是因为认床,还是深山鹧鸪,杜鹃啼血扰人清梦。
半睡半醒之间,忽见三四个黑影欺近,不由一哆嗦,整个人都清醒过来了。
钟若瑜十分警醒,立刻张开眼睛轻声道:“怎么了?”
渔舟未答话,伸手指了指移动着的黑影。
钟若瑜纵身一跃,几个起落间到了黑影处,忽而轻笑出声,回来时手中提着三个瑟瑟发抖的孩子。
“小兔崽子,不睡觉想做贼麽?”钟若瑜低笑道。
三个脑袋连连摇头,拨浪鼓似的。
“快放下他们吧。”渔舟轻声道,“可是没找到家人,然后夜里又冷得厉害?”
“我们只是……只是想离火堆近些,并非……并非心怀不轨。”为首的男孩瑟缩着身子哑声道,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另外两个更小孩子。
“没有多余的大衣了,你们仨将就些吧。”渔舟坐起身子,将自己的大衣递给了那个男孩。
男孩伸出双手接过,十分恭敬地行了一礼。
“便宜你们这些兔崽子了。”钟若瑜轻哼道,伸手拿起自己的大衣欲递给渔舟。
宣竹不知何时竟然醒了,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侧过身子,一把揽过渔舟,将她按入自己的怀中,然后又仔细地裹好了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