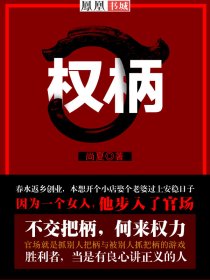她不知道,这个茶座是他开的,这里的服务员,都对他唯命是从。
水仙一坐定,就想他说春水的事。她知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随身带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五千元,这是好处费。
她把信封推到副主席面前,说这是一点小意思。
从前,他就会爽快地收下,这一次,他看都没看,眼睛看着她,直勾勾的,一会看脸,一会看胸。
她对他说,快说吧,什么情况。
他好一会才收回了神,慢悠悠地吐着烟圈,说有人想杀春水。
她心里一紧,问是谁。
他问她,是不是想救春水。
她说春水是好人,谁都想救。
四十三
他故伎重演,说想救春水,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她问此话怎讲。
话说到这儿,他就不隐瞒了,表示只要她跟了他,他就能救春水。他上面有人。
水仙强忍住内心的厌恶,说他是受人尊敬的领导,有家有室,儿子都快要成家了,这样说不合适。如果能救春水,需要多少钱她愿意出。
他脸上的笑容收了,换上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说别给脸不要脸,一个开小饭馆的,有什么了不起。
水仙听不下去,起来想走。他开始撕破脸皮了。
人一撕破脸皮,剥下了伪装,流氓重归于流氓,强盗现形为强盗。
他一手拉住了她,说想走没那么容易。
水仙下意识地甩手,一下子就挣脱了。
他走到门口,拦住了她。
她大声喝着,让开。
他看着因为激动紧张而颤抖的她,一阵狂笑。
她想挤开他。可他体形庞大,足有一百八十斤,挡在门口,就象肉砌成的墙。
他伸出手,想扯她的衣服。她往后退了一步,重新坐定,对他说,不用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他狞笑着,说知道就好,那就从了他。
她见他铁了心,知道已经无从说服,就大声喊服务员。可整个茶座好像空无一人,任凭她喊破喉咙,人影不见一个。
他又是一阵狂笑,抒发着内心的得意。这是,这是他的地盘。
见没人来,水仙倒镇定了,毕竟,他年经比她大两轮,一对一,就算占不到上风,也差不到哪去。
水仙劳动人民出身,又练过体育,要扭打起来,一般男人都对付不了。
他见水仙不叫了,坐在那里很淡定,以为她怕了,软了,就要从了。
他坐到水仙身边,说这就对了,不就是玩玩,何必那么认真呢。跟他上了床,又不会少了什么东西,相反,还能得到许多好处。
他的手就往水仙胸上放。
水仙抓住他的手,用力一拽,他防备不及,站立不稳,差点摔倒在地。恼羞成怒的他,站定以后,想一个巴掌掴过来,水仙退开了。
他这才知道,低估了这个女人。
不过,他有后招。一人制服不了,就叫帮手。
这里经理,是他一手招聘培养起来的,对他言听计从,十分忠诚。他按了下铃,就有一男一女进来了。
他们经过演练过一般,进来后就到了水仙的身后。
女的拦腰抱住了她。水仙被这突然的变故搞蒙了,这女的挺壮,一双手粗壮有力,箍在她的腰间,一时令她无法动弹。男的死死抓住她的手。他们在等副主席进一步的指令。
副主席很生气,手在水仙的脸蛋上捏了捏,说:“臭女人,给脸不要脸,我看你还能怎样。你们把她绑起来。”他看了看,“对,就绑在这张太师椅上。”
一男一女得到指令,就把她摁在椅子上,拿来绳子,把手脚都捆了。水仙挣扎了一阵,却无济于事。这一男一女似乎是捆绑的专家,严严实实的。
工作完成了,副主席一挥手,他们消失了。
副主席拿了张椅子,坐在她的对面,翘着二郎腿,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了一长串烟圈,往她的脸上。
她低头皱眉,躲避着。他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然后又是哈哈大笑。
“你这是何苦呢?挺简单的事,搞得这么复杂。”他说道,“我只是想和你睡觉,想看到你脱光,又不会吃了你,你何必这么抵触呢?”
他顿了顿,又吸了口烟,吐在她的脸上,接着说:“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但这个样子完全是你逼我的。只要你同意跟我,我立马放了你。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好吗?”
水仙有些发晕。她眼睛空洞地望着对面的墙,忽然发现,雪白的墙原来是黑的,黑得让人心慌。她经历过不少居心不良品德恶劣的人,曾以为,不会遇到下一个了。可下一次出现的,往往更加穷凶极恶。也许,这是她的命。
她是不认命的。就算面对的是绝望,她也会拼死反抗。
用力挣扎的后果,就是绳子上沾满了鲜血,她太用力。
副主席假做怜惜,说:“你这又是何苦呢?”
她已不想和他说话,不想看他。
死不足惜,她牵挂的是女儿。如果春水能平安无事,希望他能把女儿抚养长大。
她的决绝震慑了他,他一时不敢造次。可面对到手的猎物,他怎么可能良心发现,就此收手呢?
他只想让她平静下来,接受这个现实,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她离了两次婚,早已不是什么清纯女孩子,睡一觉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他的头脑里,完全用不着以死相拼,这只有傻子才做的事。
他相信对面绑着的女人一点不傻,相反,还非常聪明。
他端起一杯水,让她喝,说只要她点个头,他马上叫人松梆。
没有想到的是,走到近前,他得到的是一口唾沫。
这个他恼了,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结结实实的,嘴里还骂着:“臭婊子!”
他用力扯下了她的上衣,露出胸罩。他眼睛亮了,这正是他想要的。不问三七二十一,他像条疯狗一样,一阵乱咬乱扯。
她的上身被完全裸露了。
狞笑变成了淫笑。
他好象记起了什么,从边上拿起一个包,掏出相机,一阵乱拍。
他曾经被人称为艺术家,也是县摄影家协会会员。当初,他就是想拍光身女人才迷上了摄影。有些漂亮女人,需要留下一个永恒的记忆。当然,相机还能偷拍偷窥,现在的机器越造功能越强,几十米几百米外的女人,都能用镜头捕捉得清清楚楚。
按理说,他这样有钱有势的,不需要偷看偷窥,直接上不就完了。但偶尔的偷看偷窥,是一种乐趣,他乐此不疲。
他甚至会安排自己的情妇在某个角落脱衣裸露,然后他躲在远处拿着相机一阵拍。事后,他又觉得这种刻意的安排已失去了偷看偷窥的神韵。
他不断地升级设备,就连最专业的摄影家,都自叹弗如。当然,这钱不用自个掏腰包。领导搞摄影,哪有财政不支持的?
领导搞摄影,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拍女孩的身体了,她们是模特,他是艺术家,有人非议,就是不懂摄影玷污艺术。
遇到身材火辣的女孩,他就会对她说,聘请她作为模特,价钱好说。他态度诚恳,目光坚定,看上去象个艺术家。一些女孩就信了他,这个年龄上可以作父亲的人。
有了第一步,就有了第二步,第三步。他利用权势,运用手段,不知使多少女孩上了当。
他看上水仙,就是因为她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吸引着他。他曾经在本子上写过,水仙是西方女人与东方女人的完美结合。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美,在她身上呈现了。
他非常渴望能见到她的*。
没想到的是,她软硬不吃,手段用尽,却不能上手。
绑住她,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这出现了另一种美,扭曲的畸形的美。
他想到一个标题:受难的鸡女。
他咽了咽口水。
他这个年纪,已没有年轻时的生龙活虎,有时只想观看玩赏,而不是占有。
虽然他不惜重金,四处搜罗能恢复雄风的药,但那种东西不能多用,否则就会头晕目眩。
他想象着能与水仙轻柔温存一番,而不是现在这样霸王硬上弓。
拍完了上身,他意犹未尽,又想脱她的下身。
对于水仙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她的眼神如刀一样地射向他。
这并没让他退缩,他觉得这种眼神正是他的照片需要的。
她恨不得把他的相机砸得粉碎。
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正面背面,全身局部,他拍个不停。
他还有个考虑,这此照片将是威胁她的手段。
女人私下里都极爱面子的。
阳光下的罪恶。上午九点多钟,水仙来的路上,阳光很灿烂,她的心情不错,觉得此行肯定会有收获的。
后悔已经晚了。她身上渗出的血滴在了地上。
她想与他同归于尽,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她在坚持着,不让恐惧完全地攫取了自己。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得撑下去。
有一个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只有十八岁,是这家茶座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