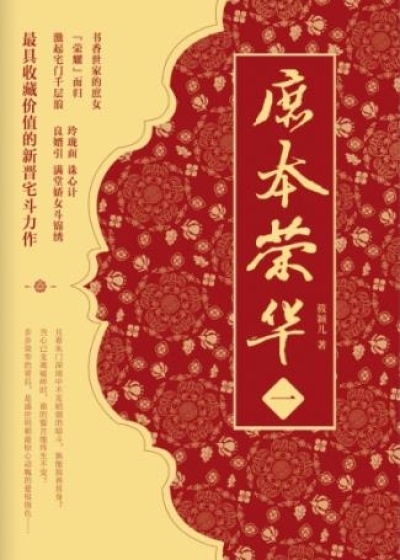景秀去看望白苏,见得廖大夫为她把脉,便坐在一旁候着,稍后等廖大夫请脉完毕,但见白苏迟迟不醒,想起霍氏的情况,她担心地问:“白苏怎么样了?”
廖大夫坐下来,执笔开了张药方,边道:“好在没伤到要害,额上浮肿,得长些日子才能消肿,我开些化淤的方子,每日吃两剂,再用祛痕的膏药敷一敷,年轻姑娘家的落下疤痕,就坏了。”
景秀默默听着,望向躺在床上的白苏兀自走神。
廖大夫将药方理好,递给景秀,见她颜色如雪,并无一点血色,眼眸昏沉,气息微细,便拢了袖子,伸手搭在景秀脉搏上。
景秀手一惊,欲要抽回来,廖大夫用力按住她脉搏,“别乱动,我给你看看。”
细诊之后,廖大夫捋了捋胡须,沉思片刻才说:“最近药服用的如何?”
“每日都有在吃。”景秀如实道。
“偶尔会有咳嗽吗?”廖大夫又问。
景秀嘴微微张了张,却没有说话。
廖大夫见了,叹息道:“时有咳嗽,吐出的痰还带点血?”
景秀睁大了眸子,看着廖大夫,廖大夫和蔼的笑道:“行医三十载,你这病只需看脉就能看出,瞒也是瞒不住的。”
她眸中波澜不兴,屏一屏呼吸道:“我的病很严重了吗?”
“都吐血了,能不严重?”廖大夫一幅明知故问的模样瞅着她,“少年吐血,年月不保。你这丫头是嫌自己命太长了,还不知怎么照顾自己?”
景秀眉心微低,面上卷起暗垂的铅云。
廖大夫见此叹道:“郁气伤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气不定,胸闷咳血。你的嗽喘之症本多是自身情绪所致,不可动怒不可忧思伤感,每次动气伤怀则病加重,所以喝再多的药都无法根治,想治得几分还得靠你自己调理,再这样不爱惜自己,真是大罗神仙也难的救你,可没多长的命续了?”说到这话,见景秀不无动容,他摇头晃脑的摆着,又叹口气道:“我岁数大了,真看不懂你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家,是有多少感春悲秋的事让你伤感成这样的?”
景秀只是苦笑道:“这病我也不知该怎么办?”
廖大夫劝解道:“活到我这个岁数,许多事都能看的开,过多的纠结只会害自己痛苦。想想人生这匆匆数十载,总惦记那些烦心事不是自讨病害。你啊,就是心事太重,藏在心里成郁气,再不排解出来积压着,等到有一日受不住了,你才晓得后果,等那时你再想通也为时已晚。你看你这也到了成亲的年纪,让你父亲找个好家世好人品的过着日子,家里不顺心的事能忘就忘,换个地方,也许就淡忘了,再去外头多游玩逛逛,看看风景,心情开阔了,病也就好了一半。”
景秀含笑着听在耳里,“哪有您说的那么简单?”
“是不简单,你们这些小辈哪里容易参透当中的道理。”廖大夫笑了笑,也不再多说,便又研磨执笔写下药方,一面道:“郁火太旺,我看你过去的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多了些.虽说益气补神,可你现下的病情也不宜太热。依我说,还是要用敛阴止血的药,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我这里得了民间私传的偏方,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你暂且吃一吃,但那药也别停。”
景秀颔首,接下药方,看了看,苦笑道:“我算是得了富贵病了,燕窝吃起来不便宜。”
廖大夫呵呵笑道:“现在理家,还会精打细算了,你这丫头,还真不知谁有福气娶了你?”背着药箱站起身。
“我一个病秧子,谁愿意娶了?”景秀打趣着,亲自引路送他出去。
路上,景秀还犹豫着问道:“我母亲的病如何了?”
廖大夫脸色有些沉,琢磨着道:“方才我去给你母亲诊过脉,病没起色,反而更虚了,我看情况不大好。这每日的药都是经你手的吗?药剂药量的火候拿捏的是对的吗?傅太太的病这段日子尤为关键,千万不要马虎大意了。”
景秀轻轻地“嗯”了一声,轻拂衣上尘灰,道:“我会好好照顾的。”
送走廖大夫后,景秀去了霍氏内室,正看到景沫坐在霍氏床头,安静的端坐着,纤细的脊背挺的笔直。
听到背后的响动,景沫回过头望着景秀,半带轻笑道:“你似乎忘记了我先前跟你说的话?”
屋子里服侍的丫鬟听到景沫这句,全躬身退出去。
景秀见房门带拢,眼波一定,反问道:“什么话?”
景沫抿了抿嘴,冷笑一声道:“难怪迟迟不见动静,原来早盘算好了心思应付我。”末了,又自言自语的添加一句,“你的本事真不小。”
景秀狐疑的看着她,不解她说这话什么意思?
但听她转了语气,和悦了神色地舒缓问道:“景秀,我很想问你,睿表哥,邵大人,还有……玲珑十二馆的四叔,你心里更喜欢谁呢?”
景秀嘴角微微一动,并没有接她的话回答。
景沫静静的等着她答案,却见她迟迟不张声,眼底含了稀薄的冷意,左右认真将她打量着,良久过后,嘴里轻飘飘的吐字道:“你心里连喜欢谁都不知,我真看不穿他们到底是喜欢你什么?又看上你哪点?长的漂亮吗?我自问也不比你差,难道是心地善良?可你是如何进府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的心又能善良到哪去,你那般心狠手辣连我都自叹不如?”
看着景秀面无表情的那张脸,景沫略顿了顿,咬着贝齿,似笑非笑地道:“我猜,大概你跟你姨娘一样,都会那种勾引男人的本事,你更是无师自通,让他们对你神魂颠倒不成?”
景秀听到她这样说娘,面上不自觉地搐起,和太阳穴突起的清淡青筋一般,昭示着她发自心底的愤怒,一颗心跳的厉害,气郁发作。
可是抬起眼在看到景沫那张笑意更深的面颊时,她强自努力的镇定下来,想起刚才廖大夫那番话,她不能让自己太动气,不然就着了她的道了。
景沫不似景汐那样莽撞好骗,也不似霍婷婷野蛮心狠,几句言语冲撞就能让她们原形毕露。显然景沫的能耐更高,她拿这个来说,便是要激怒自己。
怎能轻易被她言语就戳到软肋!
想到此处,景秀无表情的脸上渐渐浮起一丝笑意,淡薄的笑意如绽在风里的颤颤梨花,她按住心口的位置,微微笑道:“四叔温柔脉脉,对人说话总是笑如春风,又见多识广,和他一起聊天闲话时,许多烦躁都能淡忘,这样的人,实在很令人吸引着迷,试问我怎么不会对他动心呢?”
景沫似是信了,藏在袖子里的手紧了紧,眼睛里的光亮如火在灼热,到底是压下来道:“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景秀嫣然一笑,明眸中水波盈动,已微微含了几分清亮意韵:“什么人什么身份我不在乎,我喜欢他这个人,又不是他的身份,不像大姐姐原来是喜欢他的身份啊!”旋即露出一抹鄙夷的嘲笑,冷眼看着她啧啧地道:“怪不得四叔对大姐姐的那番真情惬意视若无睹了,竟是居心叵测!四叔虽说腿脚不便,但心里比任何人都看的清楚,也更分明,你的那些鬼魅伎俩恐早被他识破,他又岂会对你有丝毫动心,有的只是厌恶、鄙夷、嘲讽、恶心……”
她每说一个词,便咬重口气一分,看到景沫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她心底竟是异常欢愉的。你知道我的软肋,难道我便不知你的?
认真你就输了!
“你闭嘴!”景沫咬着牙听她说完这些,再也忍不住的倏地站起,脸上涌动着源源不尽的愤怒,她高声喝道:“在你没进府之前,他的温情全都只给我一个,只会对我温柔笑着,也只会开解我帮我。是你使了那些狐媚手段勾引他,他才会对我恍若不见。傅景秀,你又有什么资格说我居心叵测,你才是居心不良,你为回府向你亲哥哥下毒。为对付母亲对付我,便几次偷偷跑到玲珑十二馆去,若不是你三番两次如此,我也不会为打击你,做那么多事,让父亲和妹妹们对我失望。”
她索性摊开了道:“你的回府就是你精心设计的阴谋诡计,目的就是为报复我们这个家。你小时候指着傅家大门,说如果有一日再回府,必将让我们不得好死!你现在全都做到了,你害的母亲不醒,还让父亲把这个家给你打理,下一步你是不是要让我们整个傅家家破人亡?傅景秀啊傅景秀,你真真是狼子野心,城府极深,还敢跟我说那些话,你又好到哪里去?”
她伸出素白的玉指,指着景秀的脸面,一气不停的道:“傅景秀,你就是个贱人,你跟你姨娘一样,都是贱人!”
景秀不恼,反而微笑着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