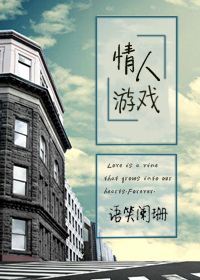从丞相府回到少府寺,徐仁还没有进门,一位少府丞就匆匆走了出来,一见到徐仁,当即便大喜过望,行了礼就对他道:“皇后还未央宫,有诏令君觐见!”
徐仁一愣,回过神来,脱口而出地第一句话就是:“诏我觐见?”
那位少府丞连连点头:“正是!臣正欲往丞相府寻君。中长秋尚在堂上相候。”
徐仁不由抬手揉了揉是眉心,心中嘀咕了一句:“先是大将军,这会儿,中宫又诏我做什么?”
虽然满心不愿,满腹疑惑,但是,皇后的诏令,终究是不能不理的,徐仁只能先往少府正堂与中长秋相见,再随其往椒房殿而去。
一路上,徐仁也试着问了问中长秋,可是,中长秋也只是苦笑摇头,只道自己实不知情,徐仁只自己揣度着,想了半天,也只能往之前皇后之诏被封还上想。
眼见着将过椒房殿前的两出阙了,徐仁硬着头皮问道:“中长秋,望君实言于我,中宫可是为诏书封还一事……恼怒?”
中长秋一怔,随即摇头,却是笑着答道:“中宫并无恼意!”
见徐仁不信,中长秋看了看左右,压低了声音道:“中宫当谢君等。非少府封还中宫诏,中宫岂能今日还宫?”
――的确,皇后向皇帝请辞时,就是用的这个理由。
――当然,皇后也借此向皇帝讨了手诏。
中长秋并不认为,皇后会为那件事对少府不悦。
徐仁松了一口气,随即也更加疑惑了。
中长秋与少府在椒房殿的前殿等了一会儿,皇后才从后殿过来。
见礼之后,不等徐仁开口,兮君就直接道:“掖庭之中,侍使之人甚少,少府可有主张?”
徐仁没有想到,皇后竟是为此事宣召他,当即就愣住了,心中也十分惶然。
――禁中之人事,他都不能过问,何况掖庭?
惶然之后,徐仁将心一横,直截了当地答道:“掖庭之事,中宫当问掖庭令。”
话一出口,徐仁竟觉得理直气壮了。
――本来就是如此嘛!
心中一松,徐仁倒是困惑了――就算皇后年幼无知,不知道少府的实际情况,中宫属吏难道也不知道?
――更何况,皇后年幼无知?
徐仁很确定――年幼是事实。无知?那是不可能的!
――若是无知,皇后能与上官家的谋反毫无关系?
――当然,“毫无关系”这个事实,其中肯定有霍光的原因,但是,若不是皇后有所表现,霍光凭什么维护她?
徐仁绝对不相信,这位年幼的皇后会是多么天真,多么无知……
“掖庭之事自然是掖庭令作主。”兮君并没有为徐仁的态度动怒,依旧以温和地语气地言道,“然则,掖庭令欲增补缺员,却不得不由少府供人。”
徐仁一怔,随即便解释:“臣未见掖庭有增补之请。”
――绝对不是他不配合掖庭之事。
见徐仁如此紧张,兮君倒是有些奇怪了。
“少府……”兮君皱眉,解释了一下,“我并非问责于君。”
――难道她的态度很恶劣吗?
兮君看了一眼身边的傅母,傅母却也回了她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
――并不是皇后的问题。
徐仁低头:“臣明白。”
虽然这样了说了,但是,殿中众人仍然看得出这位少府十分紧张。
想了想,兮君也就将这个想不通的疑惑暂时搁下,慢慢道:“掖庭令云,少府属下各官皆有定员,今已无可调之人。”
徐仁一怔,回想了一下前几日所收的文书,立刻点头:“的确如此。”
兮君十分满意地颌首,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这让徐仁不由困惑了。
“既然如此,不知道少府有何应对之策?”兮君轻声询问。
徐仁思忖了一下。
――虽然迁任少府不无田千秋之关系,但是,他本身也并非无能,至少,谈不上尸位素餐。
片刻之后,徐仁答道:“若是宫人不足,自然是增选官婢。若是宦者不足,就只能调腐刑之人,再不足,尚可募死罪下蚕室。”
――这些都是定制。
――皇后有必要这般郑重地诏他前来吗?
这一次,皇后没有立刻回答,好一会儿,才慢慢道:“掖庭不比其他官署。”
徐仁顿时一惊,暗暗着恼――自己竟然忘了最关键的事情。
――掖庭是什么地方?
――说白了就是蓄养皇帝的女人的地方。
――那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贵人。
――更重要的,那些人是为皇帝准备的,必须精心服侍,精心教导……
――无论如何,在掖庭侍使的人,都不是随便选哪一个都可以的。
徐仁不得不向皇后请罪。
兮君摆了摆手,并无恼意,道:“少府似乎……另有心事,对答有误亦属寻常。”
徐仁连连称谢,随即小心地答道:“掖庭甚重,臣一时亦无良策,若中官准允,臣将召诸属吏共议,议后即报中宫……”
这一次,徐仁半点风险都不愿担了。
兮君扶着凭几,良久未言,直到徐仁满头大汗了,她才轻轻地嗯了一声:“此事当尽快处置。”
“诺!”徐仁连忙伏首应下。
等了好一会儿,徐仁仍然没有听到声音,正在着急,就听到一阵悉索声,随即就是玉佩相击的声音,听着那声渐渐远去,徐仁才慢慢地直起身,果然看见,上席的绣幄中已空无一人。
中长秋走了过来:“中宫命臣送少府。”
“有劳中长秋。”徐仁连忙客气地谢过。
出了椒房殿,徐仁抹了抹汗,揉着额角,对中长秋道:“中宫为何对掖庭之事如此上心?”
中长秋看了看左右,见周围空旷无人,才轻声回答徐仁:“中宫上下都对掖庭上心。”
徐仁一怔,立刻就回过味来。
――原来如此啊!
――掖庭中都是皇帝的女人,皇后……怎么可能不上心?!
――自己竟是多此一问了!
这样一想,徐仁连忙谢了中长秋的提点,随后又低声问中长秋,中宫是否对掖庭侍使之人有什么要求。
中长秋见徐仁如此问,虽然心中很满意,但是,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道:“少府按制行事,中宫素来依制守礼,岂会另有它言?”
徐仁连连称是,心中却暗骂自己――怎么尽问这般愚蠢的问题了!?
中长秋也觉得少府今日的举动十分奇怪,不由也问了一句:“少府今日……家中有事?”
――虽然言及其私,但是,也是委婉地询问了。
徐仁连连摆手,却没有答话,半晌,将出禁门了,徐仁才叹了一口气,对中长秋道:“君不知……皇后诏我之前,大将军遣长史致言于我……”
说着,徐仁又叹了一口气,但是,到底没有说出,霍光究竟让人对他说了什么。不过,看看徐仁的神色,中长秋又怎么可能猜不到呢?
中长秋不由满脸怜悯地看了少府一眼。
――难怪这位公卿大臣,在椒房殿的应对那般失态了!
椒房殿中,年幼的皇后也对傅母说了相似的话语:“少府今日……似乎十分惊惶……”
傅母点头,不过,她并没有往霍光身上想,而是揣测:“也许是因为此前封还皇后之诏……”
兮君点了点头,却并没有往心上去。
一行人簇拥着皇后回到寝殿,皇后却在殿门前止步。
“傅母随行,余等不必入内。”兮君对众人吩咐,倒也没有让他们都在殿外候命。
众人自然应诺,等皇后与傅母进了殿,殿门关上,一干人留了两个人在殿外候着,其他人就先往庐舍去了。
――十月了……
不管殿外如何,后寝之中,仍然是温暖如春的。
温炉中,黄澄澄的火焰看着就让人觉得暖和。
也许正是因为太暖和了,内卧之中,刘病已只觉得满心的焦躁不安,最后实在按捺不住,只能在殿中来回走动,但是,他也知道不能弄出动静,只能继续压抑,因此,也就更焦躁不安了。
兮君有些奇怪地看着刘病已明显不安的举动,只觉得自己完全无法理解。
――有必要这样担忧吗?
兮君觉得刘病已对这件事太过上心了。
――那位宦者丞值得他如此重视?
兮君思忖――或者,这是掖庭令的意愿?
“兮君!”刘病已总算发现了站在内户外的兮君,立刻唤了一声,走了过来。
当然,他那个欣喜的呼唤也换来皇后傅母的一个瞪视。
――他可不是正大光明来这儿的!
兮君也翻了一个白眼,没有理会刘病已期待的神色,径自走进内卧,在床上坐下,又将旁边的玉几拉了过来。
傅母没有进内卧,而靠着内户旁的帷帘坐下,目光则一直若有似无地跟着皇后。
“兮君……”刘病已在床旁跪下,再次唤道。
“小哥哥……”(注)兮君皱眉,“小哥哥为何如此关心无关之人?”
刘病已一愣,随即便摇头:“许丞不是无关之人。”
兮君更为不满了:“纵然其对君有恩,汝为之请得免死亦可偿也。”
――其实,不止是免死了。
――死刑的下一级是城旦舂,再下一级才是鬼薪。
兮君觉得,刘病已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热切地期望将那个人留在宫内。
――鬼薪的刑役再重也有限,毕竟都是为官署之类的执役。
刘病已被她问得语塞,好半晌才答道:“不是……”说着,他也皱了眉,十分苦恼于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
“许家人一天不落地去张令家哭求……我实在……”
“……受不了了……”
注:虽然到现在都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我还是说明一下吧,汉代是没有“哥哥”这个词的,哥在当时是通“歌”的,“哥哥”这个词可以算是外来词,是从鲜卑语音译之后又进行了转换的词。成为兄长的同义词更是要到唐代中期左右。不过……我还是喜欢小女孩这样喊半大不小的少年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