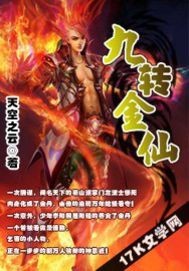“长御,考虑将来已是奢望……”
倚华拜伏于皇太后的身前,耳边却仿佛听到另一句相似的话语。
——身披锦绣绛袍的少妇无奈闭眼,委婉却坚定地拒绝她的恳求,哪怕那恳求也是皇后的意思。
——“但是,若没有将来的希望,我等如今为何努力?”少妇睁开眼,黑眸中一片清明。
清晰的记忆让倚华不再踌躇,微微抬头,对上官太后道:“陛下,令堂敬夫人曾对婢子说:‘若没将来的希望,我等如今为何努力?’既然将来仍可期待,陛下又岂可抱持如此想法?婢子恳请太后三思!”
“先妣……说过这样的话?”与皇太子刘奭一样,在上官太后的心目中,早逝的母亲是完美无缺的存在,除了满心孺慕便是满心追思,听到倚华这样说,她实在是无法不动容。
“是的。”倚华直起腰,长跪在她面前,神色郑重,“当日,思后只求能保住今上的性命,哪怕隐姓瞒名、一生卑贱,可是……令堂不答应。”
上官太后深吸了一口气,默默转开脸:“我明白了。”
——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挣扎,而是要为了将来的无限可能努力活下去。
*****
穿过长街直道,皇太后车驾由长乐西阙进入长乐宫。上官太后居于长信宫,马车沿中宫内直道缓缓行驶,刚看到长信宫前的三出阙,坐在前舆的御者就听身后有人轻击木隔,连忙询问:“陛下有何诏令?”
“停车。”倚华轻声吩咐,“陛下想步行。”
“诺。”御者不敢怠慢,扬鞭空甩一下,清亮的呼哨声已提醒属车随从注意动向,随后才缓缓拉动辔绳,停稳马车。
随行的侍御立刻搬来木阶,倚华推开车舆后户,俯身恭请皇太后下车,自有侍御低头上前,伸手扶持上官太后步下木阶。
稍理了一下曲裾佩绶,上官太后抬起头,微微摆手,示意众侍御退下:“倚华同行,尔等自便。”
“敬诺。”
步下车驾,倚华匆忙跟上已经往酒池行去的皇太后,心中却十分不解,但是,上官太后明显无意多说的姿态让她只能沉默。
沿着条砖铺设的露道缓缓而行,倚华只能听到皇太后脚下的黑舄轻击地面的声音,随着那一声声有节奏的轻响传入耳中,倚华的心不由就提了起来。
“长御……跟我说说先妣吧……”上官太后忽然开口,声音很轻,语气幽然,倚华差点没有听清。
“敬夫人……”倚华稍稍愣了一下,不知该从何说起——毕竟,她与皇太后那位追谥为敬夫人的生母并不是很熟悉。
霍光的嫡女,上官桀独子的正妻……即便她是皇后的亲信,也很难让那位少妇多加垂顾,当然,那位少妇也绝对不会失礼。
“敬夫人是位很有气度的女子……”倚华斟酌着慢慢回答,“沉稳果决……”沉吟良久,她还是决定实话实说:“……与宣成侯极像。”
“……我想也是……”
虽然看不到上官太后的脸,但是,只听声音,倚华便知道她在苦笑。
“陛下……”倚华刚想开口,就见一个宦者装束的宫人从小径直奔而来,她不禁皱眉,低头不语。
“臣谒拜见皇太后陛下。”来人在道旁拜伏叩首,竟是中长秋郭谒。
“卿有急务?”上官太后停步站定,眉头也皱了起来。她自幼入宫,耳濡目染,身体力行,自然是极重视规矩的。
若是新入宫的人,她也不会计较,可是,郭谒是武帝时就司职重任的宦者,不应如此无礼。
“陛下,廷尉寺上书,请重查恭哀皇后死因。”郭谒没有抬头,语气急促地禀报。
“那又如何?”上官太后神色淡然,对他的惊慌有几分不解。
郭谒因为她事不关己的淡然而稍稍怔忡了一下,抬头看了皇太后一眼,目光扫过略显紧张之色的倚华,低下头,轻声道:“恭哀皇后免身后,侍奉女医是由陛下简定的。”
虽然只是例行程序,但是,太医令选派的女医名册都要送长信宫,经皇太后准予加玺,才会入宫侍奉。
上官太后的脸色大变,死死地盯住郭谒:“你的意思是,朕谋害了许平君!”
“臣决非此意!”郭谒大惊失色,连忙辩解,“臣只恐治狱官吏有此意!”
上官太后冷哼一声:“你是担心县官有此意!”
郭谒被说破心思,一时哑口无言,只能叩首请罪,却听倚华慢慢言道:“婢子担心县官无此意,却会以此事清理宫中人事。”
上官太后的脸色稍缓,转头问倚华:“有何可担忧的?”
倚华看了郭谒一眼,唇角微扬却没有开口,郭谒明白她的意思,硬着头皮开口:“陛下未经历过,宫中诸事皆需宫人居中相联,若是宫人皆不重陛下,臣只怕从此陛下再不闻帝宫之事。”
上官太后对权力、国事什么的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听了这话,便只是无可无不可地应了一声,却没有放在心上。
倚华与郭谒相视一眼,都有几分无奈,却陡然听到上官太后冷冷言道:“与其说卿等为朕担忧,不如说卿等为日后所恃长信宫权柄担忧。”
“臣惶恐!”郭谒是真的感到惊慌无措了。
倚华却平静地跪下,不慌不忙地解释:“婢子不知大道,却也听过‘君忧臣劳,君辱臣死。’如今东宫上下皆仰陛下庇佑,为己谋便须为君谋,请陛下明鉴。”
她的话说得如此分明,上官太后也只能苦笑了。拂袖示意两人起身,她沉吟片刻:“去临华殿,准备笔札。”
“诺。”郭谒立刻应声而去。
临华殿在淋池边,打开绮疏青琐的门户窗牖,便可见池中茭荷林立,虽然无其它景致,但是,盛夏伏暑,那千丈碧色、几点朱红的风光最是沁心。
上官太后下令后并没有传舆,而是依旧与倚华慢慢步行而来。两人到临华殿时,郭谒自然是早已将一切准备妥当。书案上端正地放着一块皇帝与皇太后专用的尺一板,旁边是苍毫笔,笔前的漆砂砚里盛着研好的墨。
倚华扶着皇太后在案后的独榻坐下,垂首在旁侍奉,轻声询问:“陛下,准备何种玺封?”这却是询问皇太后打算写私信还是玺书了?
上官太后提笔的手一顿,思忖片刻才道:“取皇太后之玺。”
倚华稍显讶色,却没有多说,旁边的郭谒立刻退到殿外,召尚符玺谒者取玺。
见上官太后落笔便书御史大夫,倚华不由讶异万分,却不敢打扰书写中的皇太后——竟不是写予今上的吗?——等看到上官太后所写的内容,倚华差点惊呼出声。
信简的内容很简单,待谒者前来奉上皇太后的螭虎钮玉玺时,倚华已将信简与封检捆绑妥当,见谒者到来,便用鎏金铜杵从砚旁的泥甬中取了武者紫泥压入捆绳经过的印齿,随后看着谒者将玺钤押其上。
片刻之后,确认封泥玺封完整,倚华才将信简重新呈给上官太后。
上官太后扫了一眼,便吩咐郭谒:“送御史大夫寺,亲交邴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