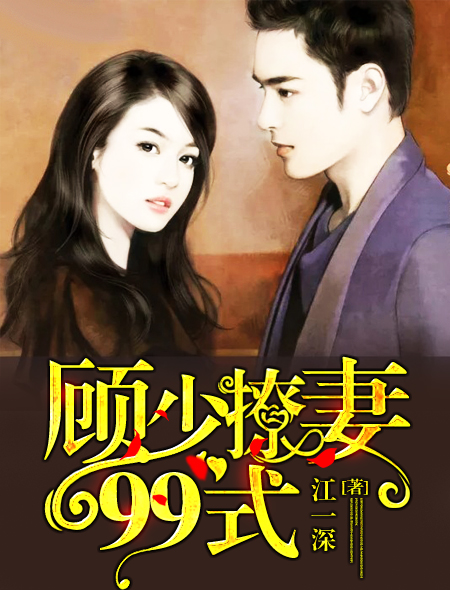桂花婶在房间里,捧着装着旗袍的盒子不知如何是好。
她老伴走了进来,他气冲冲的,五官皱在一起,看起来面目狰狞:“我早就告诉你,不要给那个赔钱货买东西,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城里人是那么好忽悠的吗?还白白损失了五千块钱,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个败家娘们?”
桂花婶一听,立刻就不乐意了,她放下盒子从地上站起来:“你说谁是赔钱货?赔钱货还不是你的女儿!这几年一直都是女儿在接济我们,你拿着她钱喝酒的时候怎么没说她是赔钱货?”
“接济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别人家的人,现在结婚了,人家还同意她那么帮着我们?你以后还不得靠着儿子!”老伴立刻就跟她吵了起来。
“你儿子多久没见人影了?每次一来就知道问我要钱,你靠往哪里去?”桂花婶擦了擦眼泪,想到她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她就觉得心脏疼。
别人都说她为儿子存嫁妆,其实都是老头子的意思,她倒是想女儿,可是每次老伴都不让。
“他以后收心了还不是伺候你?你给我去把旗袍给退了,五千块,你以为是白白捡回来的?”老伴抽着烟斗,袅袅的烟气从里面传出来,语气也是特别的刻薄。
桂花婶不可置信看着他:“你居然让我把旗袍给退了?这个尺寸是按照女儿的尺寸做的,我们现在也还可以给她寄回去啊。”
“寄什么寄?现在她的婚礼都已经结束了,还要旗袍干什么?浪费钱。”老伴对她翻了一个白眼,不以为意的说道。
桂花婶死死的抱住旗袍:“不行,我要把旗袍寄给女儿,你别拦我。”
见她不听,老伴直接拿起旁边的扫把往桂花婶的身上打去:“我让你退你不退是不是?老子的话不当话了对不对?”
桂花婶被直直的打在地上,她疼得在地上打滚,她那么一大团,被干瘦浑身没有几两肉的老伴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哪怕是被打,她依旧是把旗袍给护在身下。
当初她动这个歪脑筋的时候,是想把这个旗袍卖掉以后给女儿买一个更贵的,让她能在婆婆家那边抬起头来,也有面子。
谁知道,现在偷鸡不成蚀把米,还让她被打,她的心里又悔又恨。
要是在女儿大婚那天就寄过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
王疏清身体没什么大碍,挂了几天点滴以后就出院了。
她正在和白雪整理旗袍店,太久没有回来了,凳子和桌子上都落了不少的灰尘。
布料她从来都不会放在桌子上,她有一个专门布置的地方还保存布料,这样布料才不会有任何的损坏。
聂沧溟也在背后帮着抬水擦桌子。
刚开店,就看到一个人影从门外走来,王疏清一时间没看清,因为这人的头上还包着厚厚的头巾,看起来密不透风。
等到那人走近一看,她才发现居然是桂花婶。
这双眼睛她还是比较有印象的。
进了店里,桂花婶就把头上的东西给拿下来,她眼尖和脸颊部分都是淤青,如果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她的手臂上有被人凌虐后的红痕。
桂花婶在“枫叶镇”是出了名的泼辣,应该不至于到被人打了还是一声不吭的,王疏清立刻把桂花婶给扶进来:“桂花婶,你……怎么了?”
桂花婶把缠着的袋子给解开,这个时候,王疏清才注意到她有一个盒子。
她小声说道:“疏清,这是我之前在你这里订的旗袍,你看看能不能退掉?”
王疏清打开一看,旗袍还是完好无损的样子,她刚想点头,白雪就就从里面冲出来,冷声说道:“这是用你女儿尺寸做的旗袍,你要是退掉了,我们怎么卖出去?”
她很是不耻桂花婶的行为,见卖不到大价钱就拿过来,简直就是不要脸。
看到桂花婶的脸上留下的痕迹她一点都不觉得可怜,这种人啊,简直就是罪有应得,活该被打,得有人好好教训她才行。
桂花婶嗫嚅着没有说话,目光一瞬间暗淡下来。
良久,她从凳子上站起来,直接就跪到王疏清的面前:“疏清,我求求你了,帮我退掉吧。”
要是不能把旗袍给退掉,拿回那五千块钱,估计回去也要被打。
“桂花婶,你先起来,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好好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王疏清扶住桂花婶。
她应该是被亲近的人给打成这样,要是村里的其他人估计早就闹开了。
桂花婶在他们印象里一直都是伶牙俐齿的,性格泼辣,何曾看到她那么脆弱的样子?
桂花婶摇了摇头不肯说。
无论王疏清怎么问,她都不肯开口,王疏清只好道:“如果你不说明原因,我就没法给你退旗袍。”
桂花婶心一横咬了咬牙:“你不给退,我就在你这里等到你退为止。”
“那你就好好待着呗。”白雪冷冷的说道,真以为桂花婶这个女人转性了,没想到还是跟以前一样不要脸,哪有强买强卖的道理?王疏清做这件旗袍有多不容易她又不是不知道。
王疏清在意的倒不是这五千块钱,只是原则上的问题而已。
她的旗袍本质上没出现什么问题她是不会退的。
要是以后每个人都来这里退,她还怎么做生意?
说着,她和白雪自己就忙活起来,不再搭理桂花婶。
桂花婶就一直坐着,也没有主动说任何话,也没有撒泼,就安安静静的待着,期间她还轻轻摸了摸旗袍的盒子几下。
旗袍的盒子被聂沧溟换过了,是当初桂花婶卖给陈先生时候的普通盒子,不是陈太太的那个上等盒子。
那个盒子的价格本身就不比旗袍便宜。
王疏清一直在注意桂花婶的动作,看到她摩挲旗袍的时候,她蹙了蹙眉。
桂花婶的样子明显是舍不得这件旗袍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有人逼着她,她才过来退的,王疏清迫切的想要知道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