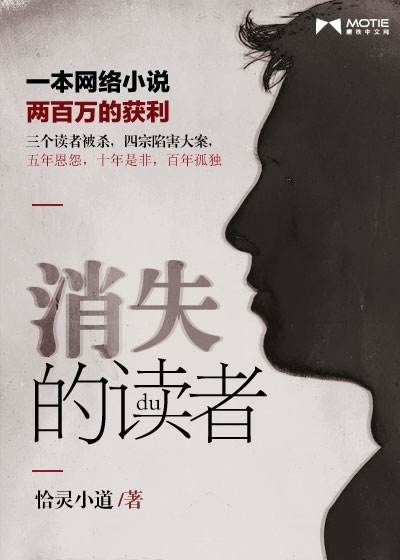谁也想不到展照白竟然突然发难。
王大人的额头被正正地砸中了,杯盏碎了,带着血落下来,场面一下子变得血腥并且触目惊心。
周围那些原本交头接耳的大人们一下子停住了,他们纷纷看向王大人,继而看向了坐在上首的展照白。
“展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王大人的眼前全是一片血红色,他抬起眼睛,一眼就看到展照白坐在上首,垂眸看向他。眼里依然是冷泠泠的,甚至没有动过半分动容的颜色。
他心里竟然一时有些发憷。
展照白道:“王大人,按律,兖州税收当三十税一,但你却私自提升收税,收到了十而税一,但兖州税收却无增长。――你倒是说说,这笔钱,你拿到哪儿去了?”
王大人眼里展现出一丝慌乱来。
他的手抖了一下,而后猛地拍了拍桌子,“还愣着干什么,谁带了帕子,借我一用!”
这屋里没有丫鬟,也自然没人能上来帮他整理仪容。他眼前现在都还是一片血色,连上首的展照白脸都看不清,只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种从内而来的压抑。
一旁的一位县令取了帕子出来,递给了他,而后看着王大人用那帕子将插进脑袋里的碎片拔了出来,而后又用帕子摁住了手上的地方,慢慢地止了血。
他这样一打岔,没有人回答展照白的话,先前那话可以说是没有得到半点回应,就石子入了海,没了动静。
王大人眼里有几分得意。――不过是个小儿罢了,怎么能真跟自己斗?
他抬起头,隔着遥遥的距离看向展照白,眼中不无得色,然而看过去,只看见展照白冷而淡漠的一双眼睛,他的话顿时便被堵住了,一句也说不出来。
而后他看到展照白向他扫了一眼。
明明人还是同一个人,但当展照白狭长的眸子对上他时,他心里顿时觉出了几分不自在的滋味来。
“怎么样?王大人想好怎么说了么?”
王大人抖了抖嘴唇,“下官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
展照白“哼”了一声,“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他手中的一册文书猛然飞了出去,王大人连忙捂住了脑袋,却见那文书落在了他前面的地面上。
他一时脸上有些火辣辣的,只好弯下了身,捡起了那本文书。
王大人抱头想要鼠窜的模样,明明应该是很好笑的,但周围的县令们没有一个敢笑出声来。今日的展照白和平素大有不同,这样的行事也是云里雾里,让他们一时都摸不出展照白的深浅来。焉知他将文书砸到王大人的脚下,不是本身就存着折辱的心思?
将文书扔错了位置的展照白端起茶盏,绷住了面上的神色。
那边王大人却已经展开了文书。
文书上面历数了他在县令的位置上所犯下的错事,一桩一件,每一件都正说到王大人的心里。
他捏着文书的手开始发抖,随后猛然跪了下来。
“大人!下官冤枉啊!”
他的额头上本来就受了伤,这会儿却不得不几番叩首,伤口处本来也不见好,却又得一次一次地磕到地面上,闷闷的声响落到众人的心里,众人一面觉得王大人这是被杀鸡儆猴了,一面第一次有了展照白此人深不可测的感觉。
展照白不说话,只静静地看着王大人叩首。直到王大人的额上重新见了血色,他才屈指轻轻扣了扣桌面,“好了,你不必磕了。”
他的目光扫过了在场的所有县令,众人都不自禁地噤声,连呼吸都放缓了。周遭顿时只能听到展照白屈指轻扣桌面的声响。
他看完了站在这里的所有人。
“今日我唤你们来,也不是想为难你们。然则陛下即将到来,总不能让陛下查出这里面的不是来。”
他有意学了他父亲说话的语调,在这样静默的环境里,只有他不受影响的怡怡然,声音落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我知道欺上瞒下这种事不止王大人一个人做得熟练,在场的诸位,恐怕没人敢说自己为民为政,问心无愧。”展照白说一半看到了一些县令抬头,欲言又止的神情,他将眼睛撇开,果然见那些人嗫嚅了一下,都不说话了。
“从前的事,我暂且不计较。但唯有一条,在陛下到来的时候,这些事,你们自己县上的事情,通通自己整理干净,不要等到我来动手。”
“――听明白了么?”
那些县令都被他压得说不出话来。
“喏。”
县令们领了命令,慢慢地退下了。
直到这些人都已不见了,展照白方才伸出手来,揉了揉脸。
转过头来的时候,依然是那个单纯的全然不像个大人的展照白。
“素白,我刚才表现得好不好?”
眼睛一眨一眨的,漂亮极了。
寒霜掩唇笑了一下,“好,好,好,大人自然是极厉害的,他们刚才可是什么话都不敢说呢。”
表扬的口吻。
展照白双眼弯弯,一下子就笑出了声来。
王大人等诸人出得府来,在门口的时候互相道别。
王大人今日出了一个大糗,面上颇有些过意不去,遂只是草草拱了拱手,也再不同那些县官们说些什么,自己独自走了。
他额上尚且有伤,想到展照白就不免咬牙切齿。
――展照白什么时候能有了这份能耐?他很是不信,定是展家派了人过来,唯恐他在陛下面前丢人才是正理。
但他向来看不惯展照白的家世,认为展某人是借了祖上荫蔽以至于今,和他这般从小苦学至今的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甩袖而行,心中郁郁不平:凭什么展某人能借着金钱就爬到他头上去?他那样一个草包,若是不将其打下来,实在是有辱读书人的斯文。
他却不曾想到,展照白虽不常读书,但为官之日,对于百姓却颇多维护,他自己虽读了多年圣贤书目,心理上却不曾将百姓当做人来看。孰上孰下,实在难听一家之言。
但王大人显然想不到这一层,他只心中悲愤难鸣,于是抬头一望天空,双手握成拳,握紧了。
却说那些大人们见了王大人离去,却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只能看向另一位也常常出主意的大人,询问道:“莫大人,不知如今,我等又当如何?”
那莫大人长了一对山羊似的眼睛,连胡须也是尖而短小的,见他们发问,那一双时常半闭着的眼睛略微睁了睁。
他道:“我等也不过是下官,所作所为,自然应该听从上峰的安排。既然展大人已经发了话,那自然应该按照展大人的说法行事。――这亦有疑乎?”
诸位大人相互对视了一眼,拱手问道:“――只是莫大人,当日收上来的赋税大都进了王大人处,而后又通过王大人递给了京中,怕是早就拿不回来了。却不知我们若将赋税调回三十税一,这笔钱,又应该谁出?”
莫大人半眯着眼睛,在月光下用眼皮将眸中神色一挡,便只剩下一点老而不明的滋味。
他摇头晃脑,说道:“不可说,不可说……”
说着便拱了拱手,也很快离去了。
留下一群人面面相觑,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过了好半晌,才有一位年轻的官员弱弱的说了一句:“那么,便按照知州大人的说法行事,不知何如?”
“为今之计,也只有如此了。”
那些县官们互相叹了一口气,各自拱了拱手,回了家去。
且不论那些县官们要各自回县怎么填补亏空,怎么将账面做得漂亮,只说寒霜和展照白提点了这些县官以后,心中便是稍定。寒霜随即叫了春风去打听,那些县官们最近动向如何。
春风却也早挂心着此事,拿了消息便极快地来给寒霜禀告:
“那些县官们倒是极乖觉的,从展大人处出来之后,回去便将此事提上了日程,不仅将税收的比例降回了正常比例,连带着对百姓们的态度也好了许多。”
“那位王大人呢?”
春风道:“亦是如此。”
寒霜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却又不免笑了一声。
“这里百姓的欢乐,竟然建立在陛下将要南巡的基础上,若是陛下回京,先前之事,怕是要重来一次。有官如此,谈何振兴?谈何民生?”
春风在一旁抓住了寒霜的手。
“姑娘,官不可兴民,臣不可兴国,姑娘大可取而代之,重塑规则。――这是姑娘一直想做的事情啊,断不要因为这些人就悲观不作为,那于这些蠹虫而言,大抵才是喜讯了。”
寒霜怔怔地看着春风拉住她的手,笑了笑,说道:“好。”
不论寒霜同春风如何作想,也不论展照白叫了展家的人去四处查访民情,也不必管这些官员们各自回去想办法填补缺口,想办法让自己表现的漂亮……十日时间一晃而过,不过是短短的功夫,寒霜便听到春风回来禀道:
“姑娘,陛下后日便到兖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