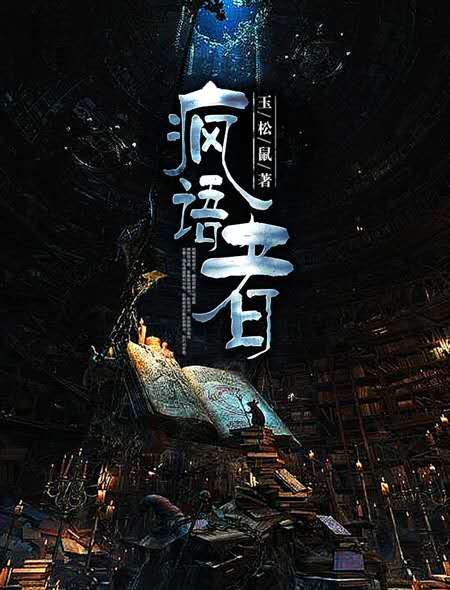我总感觉这一幕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儿。
四年前,我的一个广西的朋友告诉我他在非洲帮助贫民,自己却被传染了重病,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非洲,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把他的遗体带回国安葬。
我很感动,我觉得能放弃自己的命去换更多人的命,这就是英雄。
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非洲这片神秘的土地,燥热和大蚊子都没能吓退我,但当我到了那里,我惊呆了,恐惧了。
我第一次认识到生命的脆弱,我看到了鼠疫、霍乱、战争和饥荒,让人可以为了一口吃的不顾一切。甚至我看到一个村一个人得了鼠疫,没有药物而全村被感染,最后全村死亡的景象。
在那里人命比一棵结果子的树还不值钱,但还是有各个国家的医疗队义无反顾地帮助着他们,这让我感动,我拍了很多照片。
而我的照片中,有几张是树葬,他们将人包在裹尸袋中,挂在树上,任其腐烂。
当时,我直接向部落的酋长提出了我的个人看法,我认为这非常不安全,容易造成瘟疫的蔓延,但却被酋长制止。
他叫人将我带到了那树下,我第一次被恶心到,那树的树叶油光发亮,树干上已经不是原来的颜色,而是黑色,甚至树周围的土壤也已经发黑,有的尸体正一滴滴地往裹尸布外滴着尸油,有的尸体正在腐烂。如果这些情况你依然可以容忍,但接下来的情况你可能连隔夜饭都会吐出来。
比大拇指还大的红头苍蝇居然成群的飞,往往一只飞起来,会带着几千只苍蝇呼呼地绕着树转,那场景在炎热的非洲都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酋长说他相信他们是树的子民,人终将尘归尘,土归土。
我有一肚子的道理可以反驳。但他又却将我带到了一个小小的屋子,那屋子很阴森,地上不过有两米,但地下至少有十米,我们顺着深深的坡道儿走进去后,里面有股淡淡的尸臭味儿。
我看到了两排狭长的架子,两边上下码放着大约有十几具裹着裹尸布的人形袋子。
酋长说这是他们有圣灵保佑的族人遗骸。说着打开了一个裹尸布,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尸体没有像外面树上挂着的尸体那样腐烂,形成尸油,而是在尸体表面形成了一层尸蜡,尸体也迅速地脱水,然后干瘪。
按道理来说,人死亡后会从内部开始腐烂,但眼前的蜡尸却不是如此,甚至它们的肚子鼓起一个大包,不同寻常地躲过了大自然的法则,没有腐烂。
不过,这我都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这些人一定吃了什么植物,而这些植物可以帮助他们的尸体躲过大自然的法则。
我带着朋友的遗体回到他的家乡广西后,安葬了他,之后我在广西观光。我再一次意外地发现了这种树葬。原来,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古怪的葬法,我们叫风葬或着野葬。
不过,看上去温柔的多,也并不把尸体放在一棵树上,而是分散在很多棵树上,我一度怀疑“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这句话或许就是来自于这里。
眼前的这树葬,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树葬,因为树葬是悬挂死亡人的,至少上面有裹尸布,而不是用来上吊自杀的。那些死人就像是怪树上结的果子,等人腐烂到一定程度,头和身子被绞手绳分家,直接从树上掉下来就是果熟落地。
言归正传,秦风看了半天,说道:“唐队,你说他们是献祭吗?”
我已经受不了这个味道,感觉张口还想吐,我拉着秦风打算回到车里再说。
就在这时,呼地一声,我隐约听到空气的震荡,秦风的反应非常地快,猛地按下我的脑袋的同时,自己也低下身子。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们头顶飞了过去。正待转身,秦风却将我一把推倒,自己也就地打了个滚儿。我手中的砍刀掉在了地上,秦风捡起一把拿在了手里。
我大骇,问道:“秦风,怎么了?”
“有东西想袭击我们!”秦风大吼一声。
就在这时,我看到那大灯照耀之下的大树猛烈地晃动了一下,有几具尸体呼呼地掉到了地上,砸出了一片臭汁烂血。
“那是什么?”我吼道。
秦风死死地盯着树上,说道:“我看不清楚!”
接着,我听到了树上发出一声凄厉的呜呜声,这声音极其耳熟,正是之前我们在营地,任玥玥听到的那种古怪的动物叫声。
我吼道:“是动物!它是夜视的,能看到我们!”
我的脑袋里轰地一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直跟随我们的动物。我一直错误地以为跟着我们的东西是跑着来的,却忘记了如果这动物是飞的,那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在别处吃饱了,随时来营地,也可以无声无息地将我们放哨的人随时杀掉。我甚至怀疑陈星的死也是这畜生干的。林黛雨上厕所的时候,它正好不在,陈星上厕所的时候,它正好飞了过来。这种随机杀人的方式,很适合飞行的动物。
此时,来不及我多想,大吼道:“秦风!回车里!”
我一边吼,一边朝着车飞快地跑了过去。我才跑出几步,就后悔了,这次,是我的紧张忘记了团队合作,而且我将后背露给了那怪物,动物法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背对着野兽,那会给它一个信号,你失去了防备。
很快,我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只听秦风朝我大吼道:“不!低下身子!快!它在你身后!”
此时,已经来不及了,我感觉到一股腥臭的风从后面扇了过来,有一双爪子抓住了我的防寒服和我的飞巾。
我只感觉脖子一紧,一股巨大的拉力将我硬生生地提了起来,我肺里的空气一下全部呼了出去,一口气死活喘不上来。
我能做的只有挣扎着双手去勒住飞巾,让那口气提上来。
我的整个身子已经离开了地面,但我可以感觉到这畜生的力气并没有我想象的大,它最多将我提起个两三米,便是它的极限。
下一秒,我听到秦风的大吼,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脚,我的身子猛地一沉,脖子被勒得咯噔一声,是断了吗?我的舌头不由自主地伸了出来,眼睛朝外鼓荡的看东西已模糊。
也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想到了树上吊死的那些“刺猬”,他们在吐出舌头的时候,会不会如我这般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