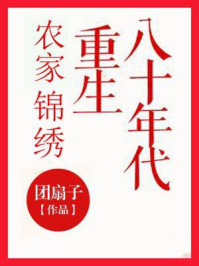霜华是河东卫氏家主卫玠的贴身婢女。
她一直以自己身份而骄傲, 她父母都是服务卫家的老人, 母亲更是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卫家的庄园,连她的名字都是公子为他起的。
公子自幼体弱,她一直紧遵夫人的叮嘱, 不能让他劳累伤怀, 这一路出行的事情, 都是她一手操办。
这次北上, 家中老夫人其实是很不愿意的, 可公子的病, 实在是拖不得了。
夫人本想亲自陪着公子北上, 却在中途病了,只能将公子托付给她和家中老管家, 加上听说大公子卫璪正在北方,只要能在蓟县汇合,便算是功成。
霜华在南方就听过很多北方的消息, 听说北方很混, 有匈奴羯人鲜卑胡滥杀人,听说北方现在是一个女人在主事——想到这点, 她就担心得不行, 连个男主人都没有, 北方怎么可能安定,公子那么柔弱的人,也不知道为看这病,要经历多少颠簸。
这次北上, 是老夫人去找她的娘家王氏出力,搭着王家的海船过来的,但以老夫人面子,居然也只借到半条船,剩下的还要用来运货,害得好多公子用惯的珍藏都没带上船,唯一的好处,就是公子没有晕船,在海浪里睡得还算安稳。
可是自从入了北方地界,便一路不顺,先是到了蓟县,才知道卫璪公子已经南下了,只留下了一座宅子让外祖家王氏照看。
下船就是一个吵闹又难闻的商市,王氏的主事却没来接他们,说是王悦公子和吴王之子因为逃课被请家长了,管事走不开身——一个管事都敢不来迎接,这简直是看不起她们卫氏。
她本想扶公子回船上歇息,公子却要提议去拜访渤海公,说是要谢谢她对兄长的救命之恩。
霜华劝了却没用,只得同意,可路上却雇个马车都雇不到,说什么公交不能被包,上了车,竟还被一个老太太欺负。
霜华就很为公子委屈,她不想再看这老太的脸,干脆轻轻撩起帘子,看向窗外,试图找出北方的缺陷,让她好好骂骂消气。
但是越走,她便越憋闷,竟是一个都找不出来。
建邺城街道狭小,听公子说,王导丞相在修缮建邺都城时,说南方地域狭小,要修得幽深些,才显得深不可测,而这里的街道宽就算了,还不知铺着什么黑糊糊的东西,竟是平整又坚硬,这马车行于其上,颠簸几近于无。
更过分的是,街上的人,基本上都有棉鞋穿!
这是什么道理,要知道,她们这些大家中顶级奴婢,也不过才得到主家恩赏了一点棉花而已,这些编户庶民,应该都穷得只能用麦草填在衣鞋里保暖才是。
更过分的是,这里人,都不给大族的马车让行,街道上一个避让的车马都没有,这如何能让平民们敬畏朝廷,敬畏官家呢?
霜华几乎瞬间就想起南方流传的,北方那女人行事粗鄙,祖上出身寒门,所以对世家严苛迫害的事实。
天啊,这该如何是好,公子接下来的日子,怕是要受苦了。
霜华一路胡思乱想着,坚定了要保护公子的信念。
“喂,已经到终点站了,你们还不下去么?”那车夫探头进来,大声问。
霜华猛然回过神来,这才发现刚刚的老太不知何时已经下了马车,那个粗鄙的车夫,正伸头进来问她。
“不是说送到渤海公的官邸么?”霜华惊怒地问道。
“是啊,可已经过站了,我刚刚喊站你没听到吗?”车夫比她还理直气壮,挥手道,“但是也没多远,你顺着这条街走通就到了……”
“不行,我们公子金尊玉贵,怎么可以走路,你快将我们送过去!”
“不能走他长腿干嘛?”车夫也每日见的人千奇百怪,岂会被吓到,当场就怼了回去,“快下去,我还要排队等发车呢。”
霜华委屈极了。
“好了,”卫玠忍不住轻笑出声,“他说得对,你们扶我起来走走吧。”
……
走在沥青的路上,那种截然不同的触感让人有些惊叹,但更让卫玠惊叹的,还是这一路的繁华。
洛阳繁华,却是贵族大家的繁华,车马穿行,但路上到处都有乞讨的贫民;建邺城繁华,是王家与其附庸的繁华,略小一点的南渡世族,也都在为重立家业忧愁;但这里的繁华,却是普通人的。
这里的人虽然行色匆忙,面色疲惫,但却没有南方庶民的谨慎与小心,看到他这等衣着华丽被簇拥的世族,也不避让,反而都是好奇地驻足打量。
路上基本看不到乞丐,到处都是带着孩子老人、神色幸福、行走在街巷的一家人——这是让卫玠最为惊叹的事情。
什么时候,庶民也有这种闲游的空闲了?
难道不该是抓紧一切的空闲时间,修缮房屋、清理农事,多做些散工,尽可能地挣一点多余的收入么?
当年卫家被迫害时,他和兄长寄人篱下,也见过贫民孤苦,这里……
“公子,这便是渤海公府邸了。”霜华指着前方的一片建筑道。
卫玠点头道:“如是,便替我送上名贴吧。”
单谦之正忙时,便收到了卫玠送来的名贴,贵族的名贴就相当于是预约,如果对方愿意接见,就会回贴写上自己什么时候有空,大家约时间一起,好让递贴子的人上门聊天。
如果是在门口递贴子,一般有关系的人都不会拒绝人家进来。
魏瑾事务繁忙,一般这些世家求见的贴子,都是由他筛选出来,总结个名单,让魏瑾有空的话挑拣着见一见。
但魏瑾每天忙都忙不过来,更不耐烦和世家拉关系,所以很久都没见了,单谦之收到的名贴一般都被拿来填档案室了。
不过,这个居然是卫玠……
单谦之想起魏瑾说过她曾经想嫁这样的美人。
“请他去偏厅歇息,”单谦之对送贴人吩咐了一句,然后便拿着名贴,施施然地走到魏瑾面前,将贴子递上去。
魏瑾以为是有什么急事,打开看了看,本想说声没空,但却突然顿住。
她玩味着拈起这张贴子:“这字倒是很有卫司空的气概。”
单谦之神色平静,看她表演。
“谦之可是不愿我见他?”魏瑾靠得近些,笑问。
“你想见谁,我可曾阻止过?”单谦之反问。
魏瑾眨了眨眼,轻声道:“这个人,可是有点不一样呢。”
“哦?”单谦之冷漠。
“他长得很好看。”魏瑾煽风点火道。
“可有我好看?”单谦之毫不避讳,问的直接了当。
魏瑾轻轻搭上他的爪子,眨眼道:“不如一见?”
单谦之矜持地点点头。
……
于是,十三年之后,魏瑾又见到了当年这位曾经想嫁的小哥。
卫玠无疑是美的,他的美,是那种玉一般温润的清澈的美好,没有攻击性,只需要静静地坐着,一卷书,一炉香,就是从画中走出的魏晋风骨。
就算病体孱弱,就算消瘦单薄,也遮盖不住他眸中那看淡生死的清澈平静,那是一种凋零之美,和这个晋朝这个时代是那么的映称。
“许久不见了。”魏瑾带着大秘书悠然走入偏厅,挥手道,“不用起身见礼了,要是站不稳还得我扶你坐下。”
卫玠微微一笑,道:“多年未见,渤海公还是如当年那般,语不饶人。”
“不一样,当年是年纪小不懂事,”魏瑾坐在他对面,给自己倒了水,“现在嘛,是随不用顾及谁了。”
“渤海公自应如此。”卫玠却是勉强起身,“但您的出兵洛阳,救下兄长的之事,却是于卫氏之大恩,仲宝在此拜谢。”
语罢,恭敬行下大礼,他姿态娴雅,毫无一点架子,真诚至极。
魏瑾有点茫然,看向自家秘书,我有救他哥么?
“徐将军出兵洛阳时,顺手救了当时被挂在战场前的一些世族,卫璪便是其中之一,”单谦之给老板解释道,“不过他因为给不出医疗费用,在上党扫了半年大街,还是王家的人过来时,顺便帮他把剩下账结了。”
魏瑾点头,这点小事,她怎么可能记住:“仲宝言重了,小事罢了,连你哥都没来说谢,哪用得着你来。”
卫玠轻笑道:“渤海公日理万机,今日愿意见吾,都让在下意外,兄长想是没能见得。”
“你还是那么会和人说话,不像有的人,连恭维都很敷衍。”魏瑾意有所指地道。
单谦之就很冷漠。
卫玠虽然重病,但打起精神时还是极为聪慧灵秀,他目光在单谦之身上划过,闪出惊艳之色,又看看魏瑾,瞬间便谨慎起来,他貌似,卷进了什么争端里了。
见那位似乎没有接话的意思,卫玠便温和地圆场道:“这世道不易,人皆有生存之法,岂能一概而论。”
“行吧,我只是抱怨一下。”魏瑾感慨道,“看到你千里来谢,我才知道这人啊,感情才是最重要的,钱财浮云,身不带来,死不带去,何苦呢。”
“这……”卫玠沉吟道,“话虽如此,然情之一字,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人身立世,还是需要一些实物方可。”
“这个不像仲宝你这种神仙人物能说出的话呢。”魏瑾幽幽道,“你以前可是视钱财如粪土。”
卫玠摇头:“三年前,吾举家南迁,方知一路民生艰辛,兄长困于洛阳,家中唯吾一名男丁,岂能再沉迷清淡玄事之中。”
“难怪王敦山简都器重于你。”魏瑾叹息道,“外貌与才华皆是上品,仲宝此次北上,可有兴趣留下?”
单谦之终于撩了撩眼皮,看了卫玠一眼。
“家母尚在建邺盼归,怕是难以久留,在下……”卫玠说到这,突然喉咙发养,以手巾捂唇,伏桌猛咳起来。
魏瑾微微皱眉,正要叫医生,便见自己的秘书已经上前,指尖一排细针,几乎瞬间就扎在卫玠身上的数处穴位之上。
“他病情极重,又奔波劳累,刚刚又强打精神应付你,扛不住了,”单秘书对老板说完,冷淡地对远处的奴婢道,“我开个方子,你去抓药,让他在这先歇着。”
那奴婢看着魏瑾,又看看单谦之,莫名不安,仿佛被猛兽按住的小鹿,眸里的惶恐都掩盖不住。
“没事,能让我家夫、丛事给他看病,算是他赚到了。”魏瑾颇有些不悦地解释道。
“奴婢不敢。”那婢女哪敢再说怀疑之语,立刻跪下求饶。
魏瑾懒得再看,等秘书写完药方,便拉着他飞快走了出去。
路上,魏老板就很生气:“你那么主动干嘛,就一点不担心我泡了他不要你么?”
“这还真不担心,”单秘书终于扬起唇角,忍俊不禁地道,“他那身子骨,你要泡了他,要不了两次,怕就是要去父留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