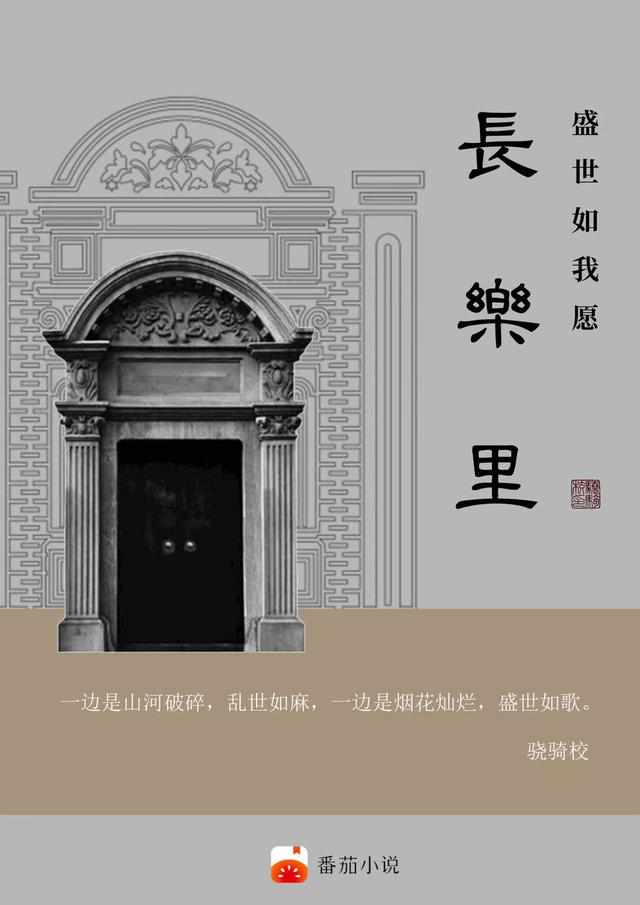第37章 顶费
对男人的那点心思,梅英再清楚不过,田飞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嘴角不由自主浮起嘲讽的笑,转而想到田飞固然是一只癞蛤蟆没错,自己却不再是什么天鹅,这嘲讽瞬间化作自怜,一声轻叹,扭转身子回去了,一颦一笑之间,看的田飞不由得痴了。
回到自家屋里,梅英躺在贵妃榻上,让小红给烟枪装上鸦片膏,侧起身子,凑着烟灯更抽了两口,忽然听到隔壁周家姆妈大呼小叫,努努嘴,小红便跑去打探,少顷回来通禀,是周家小囡肚皮痛,不知道犯了啥毛病。
梅英一骨碌爬了起来,她不喜欢周家姆妈,但周家小囡不一样,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孤儿寡母的再出个三长两短,让人怎么活。
二楼厢房内外已经聚满了邻居,七嘴八舌瞎出主意,周家姆妈乱了方寸,周家阿婆慌得在菩萨像前不停地磕头,所有一切都无济于事,小囡还是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只见隔壁梅英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烟枪,抽一口,对着小囡面孔喷下去,还别说,这一口大烟真能解痛,小囡的哭声明显没那么撕心裂肺了。
但是大烟只治标不治本,杨蔻蔻说不然送医院吧,我去叫辆黄包车,说着蹬蹬蹬下楼去了,刚出门就看到阿贵和赵殿元从远处过来,赵殿元下班后帮阿贵拉几个钟头的车屁股,两人正好在这个时间交接。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周家姆妈抱着孩子下楼上车,她一个人去怕是照应不过来,好在有个谢招娣跟着,赵殿元拉着黄包车小转弯上地丰路,迎面几个吃醉了老酒的巡警走过来,一个个面红脖子粗,皮带解下来拎在手中,敞胸露怀,行人无不退避三舍,赵殿元也把车停在路边,不想多生是非。
周家小囡的鸦片劲儿过去了,又开始嚎哭,那几个巡警闻声看过来,一个家伙喝问道:“是不是拐卖人口!”周家姆妈慌忙解释,这是我家孩子,腹痛要去看医生,巡警们围了上来,问周家姆妈要户口簿。
出来看医生哪带什么户口簿,这分明就是找茬,但谁也不敢和他们讲这个道理,周家姆妈赶紧吩咐谢招娣回去拿户口簿。
赵殿元更有经验,拿出零钱说我认罚,通常巡警找车夫的麻烦,不过就是图罚款而已,也不用多,三五个角子就能打发。
但今天似乎不行,巡警们的目光落在这辆八成新的黄包车上,车身上钉着工部局发的大照会,他们相视一笑,心照不宣,板起面孔来盘查赵殿元,说怀疑这辆黄包车是偷的,要带回警察分驻所审问。
赵殿元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这辆车既不是自己的,也不是阿贵哥的,而是借朋友的,如果被这帮坏蛋敲诈走了,两家不吃不喝白干一年也赔不起,更何况车上还有生病的小囡,他就是豁出命来也不能让车被抢走。
巡警们大怒,威胁要把赵殿元抓回去严办,正在危急关头,吴伯鸿和阿贵赶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群女人,是谢招娣把大家喊来助威的,邻居们人多势众,吴伯鸿振振有词说这是在工部局的道路上,你们警察所没有执法权,阿贵更是摆出江湖口气,放话说倒要看看,谁敢扣我的车。
巡警中的一个人,悄悄溜走去喊援兵,他们刚参加完新上任所长的升官宴,酒席还没完全散场,瘸阿宝和几个兄弟依旧在推杯换盏,听说有人在地丰路上找兄弟们的晦气,当即把酒桌掀了,拿了枪带人杀过去。
半个第六警察分驻所的人马都杀到了,这辆黄包车不扣也得扣了,瘸阿宝要立威,天王老子的面子他都不给,不但要扣车,还要抓人,不过好歹他们还算是人,没抓周家姆妈和小囡,只抓了赵殿元。
警察们带着人和车扬长而去,吴伯鸿也束手无策,只好先让阿贵帮着再拦一辆黄包车送孩子去医院,再慢慢想办法救人,赎车。
“怎么扣的,我让他们怎么给我送回来。”阿贵说。
……
瘸阿宝到底是喝大了,回去后就躺下挺尸了,睡了足足一个对时才被手下推醒,说署长办公室有电话打过来,瘸阿宝裤子都没穿,窜到墙边抓起话机,啪的一个立正:“署长好!”
“侬脑子被枪打过了?”潘达劈头盖脸就骂,“谁让侬动顾四爷的人的!”
瘸阿宝还没彻底清醒,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错,但顾四爷的名头他是晓得的,顾四爷就是有着江北大亨之称的顾竹轩,全上海滩的黄包车夫都是他的兄弟,这位大佬在沪上是最为特殊的存在,连黄老板,杜老板都得给他三分薄面,难道说今天抓的那个黄包车夫是顾四爷的门徒?
潘达发了一通脾气,语气缓和下来:“不知者不罪,把车和人放了,找个机会我带侬去向顾四爷赔礼。”
瘸阿宝挂上电话,并不急着放人放车,先泡了一壶茶,点了一支烟,他好歹也是江湖上混过的,这里面的门道清楚的很,顾竹轩名头虽然大,谁都不敢不买他的账,但是潘达的面子同样大的很,打狗还得看主人,说破大天去,也不过是一个拉车的臭苦力和一辆黄包车而已,谁也犯不上为这些大动干戈,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可就大了。
如同阿贵发下的狠话那样,巡警把扣的车还回来了,赵殿元也放了,可是人吃了一顿生活不说,车也被掉包了,本来是辆每一根辐条都擦的锃亮的八成新车,给换成辐条生锈,车厢破烂不堪的旧车,更别说最值钱的那张搪瓷牌子也不见了,工部局颁发的大照会可是有钱都买不来的稀罕货啊。
阿贵很生气,却又无可奈何,他是认识顾竹轩不假,而且是顾四爷的远房亲戚,还年轻的时候在闸北为四爷卖过命流过血,可面子只能用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登门求救,就像是小孩打不过别人总请当爹的出面一样,别说顾四爷不耐烦,就是他阿贵也拉不下这个脸。
车是朋友的,阿贵讲义气,打肿面孔也要自己出钱赔车,赵殿元更讲义气,赔钱他要出大头,结果是两家的积蓄瞬间清空,还倒欠一屁股债。
周家小囡患的是阑尾炎,送到医院开刀救治,总算是救回一条命,这一场病也把周家姆妈靠跑单帮挣来的钱花的一干二净,隔夜的买米钱都没了。
楼下吴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吴伯鸿的薪水越来越低,大儿子吴麒受了过度的惊吓,脑筋似乎不太灵光了,书也不念了,整天在家里玩耍,而且喜欢玩枪,吴太太给儿子买了一把铁皮小手枪,吴先生把巡捕房靶场捡来十几枚空弹壳,塞上弹头别在枪套上,看儿子玩的不亦乐乎,脸上带着笑,心里却酸楚的很,好好的儿子,就这么废了。
吴伯鸿以前爱喝三星白兰地,现在洋酒根本买不到,借酒浇愁也只能喝绍兴花雕,桌上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碟蚕豆,他家的娘姨也辞了,买米买菜都是太太出马。
吴太太面对着空米缸叹气,户口米能保证人饿不死,但是掺杂的沙子太多了,每次买米都跟打仗一般兴师动众的,明早又是买米的日子,得一大早叫上二十九号的邻居们一道前往,也好互相有个照应。
……
城隍庙,春风得意楼,瘸阿宝经中间人介绍,终于见到了房子卖家,在上海只有洋房别墅是可以整体买卖的,里弄不管有多少栋房子,都只有一张地契,想单独买卖的话,业主会签署一张权柄单,登记注册,证明房屋产权的变更,但在实际操作中没那么麻烦,大多是私下交易,签字画押即可。
拥有了房产,就可以对外出租,一般的做法是顶给出得起钱的人,顶费是除了房租之外,额外加在租客身上的负担,以前只相当于两三个月的房租,现在已经涨到和房价差不多了,顶下一处房子,等于获取永租权,可以继续分割出租当二房东三房东,坐收渔利。
卖家姓蒋,是个体面人,长衫礼帽,出口成章,他要卖的房子是长乐里的二十九号,民国十年建的老房子,他开价十五条大黄鱼,按照现在的市价,沪西双开间石库门房子,光顶费就得二十条大黄鱼,事出反常必有妖,但瘸阿宝不在意,长乐里是他管辖的地面,自己地盘上还能被人坑了不成,双方讨价还价,最终敲定在十二条大黄鱼。
白蚂蚁早已预备好合同和笔墨,就等着买卖双方签字了,蒋先生这才说了实话,签合同可以,权柄单拿不出来,打仗时候一把火烧了,这东西想补办也没那么容易,一来二去的就耽误了。
“不妨事,有合同就行。”瘸阿宝卷起袖子,鬼画符一样写下自己的名号:汪阿宝,又用大拇指蘸了印泥,按了个鲜红的手印。
“宝哥爽利人!”白蚂蚁翘起大拇指赞道。
蒋先生见他如此爽快,也签字画押,然后眼巴巴等着那十二条大黄鱼。
瘸阿宝将合同拿起来吹吹干,小心叠好揣进怀里,却只摸出两条小黄鱼来:“见笑了,手头就这些钱,侬先拿着,剩下的改天再给。”
蒋先生变了脸色:“勿好这样格,讲好一百廿两黄金的,侬两条小黄鱼算啥么意思。
瘸阿宝也沉下脸:“哪能!侬格意思,吾会赖侬账了,个么好了,不相信吾,这些么子拿去抵押。”
一张沪西特警总署的派司,连同沉甸甸的撸子一起拍在桌子上,枪套上还插着六枚黄澄澄的子弹。
蒋先生没想到瘸阿宝如此无赖,做中间人的白蚂蚁也傻眼了,他们是要拿佣金抽头的,瘸阿宝用二两黄金就强占人家价值二百两的房子,脸皮之厚,闻所未闻。
派司和枪是唬人的玩意,谁也不会收,不敢收,但就这样扬长而去也不合适,毕竟再乱的世道,大面上的道理也得讲。
“这样,吾写一张欠条给侬好了。”瘸阿宝也觉得自己吃相太难看,他不会写字,让白蚂蚁写了一张欠条,自己签字按了手印交给蒋先生,约定年底之前付清余下的一百一十八两黄金,逾期按照每月百分之十五收利息,这样一来,蒋先生也无话可说,只好收了欠条,败兴而归。
瘸阿宝空手套白狼,只花了二两金子就搞到一栋房子,此时他的心情正应了茶楼的名字,春风得意马蹄疾,出了茶楼,早有一辆涂成黑色的黄包车上前迎接,当了署长,出入自然要坐包车,这辆车是扣押来的,车上本来还有一张大照会,被瘸阿宝拆下来卖了二两金子,正好付了房子的顶费。
回到第六分驻所,瘸阿宝叫来一个手下,让他去长乐里二十九号通知二房东一声,重新缴纳顶费。
巡警来到二十九号砸门,正巧孙叔宝在家,笑问警察有什么事体,可是查户口。
“侬是啥么人?”巡警问。
“吾是房东。”孙叔宝依旧陪着笑。
“侬是房东?”巡警上下看看他,白相人打扮,倒不像是信口开河。
“这房子,阿拉所长盘下来了,让侬重新交一下顶费,不然房子要回收的。”巡警说。
孙叔宝大惊:“啥么子,侬所长盘下来了,这房子明明是阿拉的,从蒋先生那里花了五根大条子买下来的,手里有权柄单的,侬所长要盘,也得从阿拉手里盘啊。”
巡警也是市面上混过的,顿时明白咋回事,这大房东收了两家的钱,一处房子卖了两回,这种一鱼两吃的做法在上海滩并不鲜见,摊上了只能自认倒霉,然后看谁的背景深,手段多,谁就能抢到房子。
只是他不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瘸阿宝黑吃黑,才花了百分之一的钱就把房子讹下来了。
孙叔宝是个伶俐人,他递上一支香烟,向巡警打听了一番,终于回过味来。
这栋房子是十年前,孙叔宝的父亲花了三百块大洋从蒋先生手里顶下来的,孙家虽然不是房主,却拥有永租权,也就是说现在顶费高达二百两黄金,这笔钱应该是属于孙家而不是蒋家。
前段时间蒋先生说急用钱,想把房子所有权也卖给孙叔宝,所有权的含金量比永租权差了太多,最终花了五十两黄金成交。
这笔钱是孙家的家底子,孙家多年来吃的是从房客手中收来的房租与自家交给大房东房租之间的差价而已,孙家宁愿住灶披间,也要把最好的客堂间和厢房让给房客住,十年下来积攒的钱也就是这个数,但孙叔宝觉得值,以后二房东是他,大房东也是他,岂不美哉。
万万没想到,蒋先生把房屋所有权连同永租权又卖了一回,活活把自己坑死了。
注释:旧上海的房屋产权关系比较混乱,源于租界土地华人不能买卖,往往会找一个外国人挂名,华界的石库门房子没有单独地契,买卖靠的是权柄单,顶费又是独特的存在,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彼时上海滩居住资源极其紧张,能有栖身之地就不容易,物以稀为贵,能租到房子不但要付房租,还要租相当于房价的顶费,但拿下之后就有了永租权,房主不能随便赶你走,你有权再分割出租,甚至改变房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