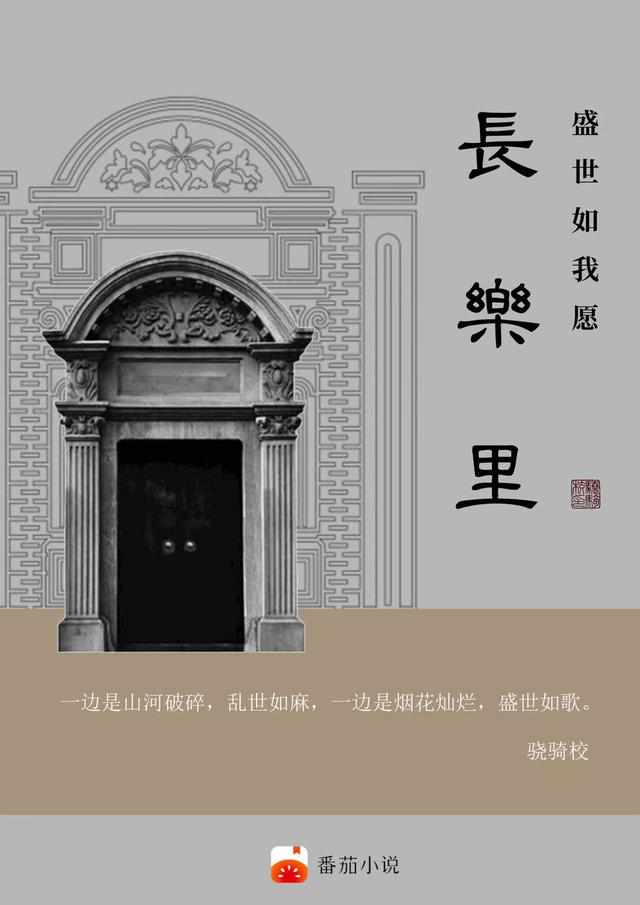第10章 孤岛陷落
盼什么来什么,赵殿元心心念念想带着杨蔻蔻登高眺远,机会就来了,厂里接了一个沙逊大厦顶楼修理烟囱的活儿,赵殿元抢着接了这个活儿,回去之后和杨蔻蔻一说,两人都激动的一夜没睡好,次日一早天没亮就起来整装待发。
家家户户刷马桶的时候,两人已经出发,清晨的空气是冷冽的,空气中漂浮着生煤球炉的味道,酱红色的电车从冬季的薄雾中驶出,犹如海底的潜艇,铃铛在响,报童飞奔着兜售报纸,车上人不多,特务们这个时段还在睡大觉,不会来打扰好心情,赵殿元眼角的淤青还在,怀里揣着饭盒和望远镜,想想在沙逊大厦楼顶野餐,他的嘴角就忍不住勾勒出幸福的弧度。
沙逊大厦是外滩最高的楼,高耸的灰色花岗岩建筑顶着一个巨大的墨绿色金字塔形帽子,特别容易辨认,这个时间点,洋行职员们还没开始上班,大门口冷冷清清,赵殿元是从后门进去的,管理员认识他,又看了看帽檐压低,穿着工装裤的杨蔻蔻。
“这是我的助手。”赵殿元解释道。
管理员木然的面孔没有一丝表情,继续看报纸。
赵殿元带着杨蔻蔻上了电梯,两人忍住笑,窃喜不已,电梯飞速上升,赵殿元讲解道,大厦下面几层是荷兰银行、华比银行和沙逊洋行,中间是华懋饭店,最上面是沙逊先生自己的私宅,据说是全上海最豪华的住宅。
“那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么?”杨蔻蔻睫毛闪动。
“恐怕不行。”赵殿元略有遗憾,电梯继续上行,叮的一声停下,两人出来又转了几道楼梯,打开一扇门,眼前豁然开朗,江风呼啸,整个上海展现在眼前。
沙逊大厦七十七米高,极目远眺,似乎连海都能看得见,两人站在大厦天台东南角,脚下是外滩马路和黄浦江,江上白帆如鲫,军舰横陈,江对岸的浦东一望无垠,陆家嘴沿岸全都是货栈和码头,再深处是住宅、村落、农田阡陌,炊烟袅袅。目光转向南,是南市老城厢,古老的,青灰色的上海县城墙依旧在,战争的痕迹已经修补的差不多了,密密麻麻全是灰色和红色的屋顶,街巷狭窄,烟雾腾腾。向后看,那是真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城开不夜的上海滩,是混居着华人、英美法人,印度人、白俄和犹太人的冒险家的乐园,西式大楼和中式民居鳞次栉比,参差有度,汽车往来穿梭,黄包车和行人密密麻麻,城市已经苏醒,进入了新的一天。
赵殿元拿出工具准备干活,叮嘱杨蔻蔻不要乱跑,在这儿乖乖看就好了。
“晓得啦。”杨蔻蔻拿起望远镜,看到平日里熟悉的建筑,就忍不住大呼小叫,唤赵殿元来辨认是不是那栋楼。
“对,没错。”赵殿元接过望远镜确认了一下,忽然眼角余光注意到江面上的动静,将镜头转过去,停在黄浦江心的悬挂米字旗的军舰炮口低垂,穿深蓝色海军服的水兵正在列队下船,登上快艇驶向岸边,这本是平平无奇的事情,水兵总要上岸的,但今天的情形明显不对劲,水兵是在刺刀枪的逼迫下离舰的,那些拿枪的兵身上有十字交叉的白色武装带,驻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就是这幅打扮。
赵殿元愕然,难道日本人对英美开战了?不可能吧,小日本再猖狂也不敢招惹英美吧,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验证了他的猜测,外滩道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开始变得稀少起来,气氛沉重而压抑,继而虹口方向杂音响起,是诡异刺耳的东洋军乐混杂着引擎的轰鸣声,重物碾过柏油路的轰隆声,外白渡桥上空弥漫着蓝色的氤氲,那是大量引擎燃烧柴油后排出的尾气形成的奇观。
先开过来的是日本人的战车队,铁甲狰狞,太阳旗刺眼,遍布铆钉的钢铁怪兽气势汹汹轧过外白渡桥,出现在外滩大道上,炮口高扬,不可一世,后面紧跟着摩托车和马队,铁骑铿锵,呼啸而过,最后是黄呢子军大衣组成的长队,浩浩荡荡,无穷无尽,雄赳赳的外国武夫,如林的雪亮刺刀,高唱着军歌开进了外滩,开进了南京路。
赵殿元和杨蔻蔻默默无言的看完了整个过程,彼此对视,发现对方的面孔都是惨白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没有什么比眼睁睁看着外敌开进家园更让人心碎的了,他们连准备好的午餐也没胃口吃了,草草完成工作,下楼回家,一路所见皆是人心惶惶。
一进29号后门,就看到各家的男主人都站在门口,神色凝重地交换着消息,突发事件打破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29号的男人们都走出各家屋门,大声聊着时局,除了晒台的小丁不在,连一向白天睡觉的田先生都难得现身了。
白先生已经登堂入室,公然以二楼大卧室男主人身份出现,他一身香色缎子睡衣,趿拉着拖鞋站在门口,油头依旧,口沫横飞:“要阿拉讲,日本人和英美开战,那是鸡蛋碰石头。”
二楼厢房门口的周阿大点头称是:“对格对格。”旁人根本看不出两家上午刚吵过一场架,周太太和梅英因为琐事拌嘴铩羽而归,自己吵不赢也就罢了,男人更没出息,别说帮老婆找回场子了,恨不得低声下气奴颜婢膝,周太太气的把厢房门用力关上,只留男人在外面讨论时局。
周阿大不生气,无论太太怎么折辱他,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浑身上下透着和气,做生意的人是讲究和气生财不假,可是泥人也有三分火气,周阿大比泥人都不如,似乎谁都能骑在他头上吆五喝六,也没什么主见,别人说什么他都附和。
吴伯鸿是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巡捕,日本对英美开战之后,原先脆弱的和平关系立即土崩瓦解,作为中国人,他在执法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倾向,以前有英国人护着他,现在全完了,英国人连自己都保不住了,所以今天吴伯鸿没去上班,在家等着消息,听了白先生的话,他心里是愿意相信的,却不开口,只是皱着眉抽烟。
章樹斋也是彼此彼此,他供职的火油公司是有美国洋行背景的,现在美国人倒台了,他的这碗饭也就吃不下去了,今天刚到公司就听说日本人开进公共租界的消息,吓得他当即收拾东西回家,打开收音机收听消息,他的看法高屋建瓴: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摸了美国人的老虎屁股,现在美国人加入战团,胜负可就难料了。
“如此说来,胜负的天平反倒是向我们这边倾斜了一点点。”田飞做出论断,油腻污浊的眼镜片今天终于清亮了一些。
“各位,以后物资可能要更紧俏了。”章先生心善,忍不住给邻居们提了个醒,战端一启,欧美和上海之间的航路怕是要断,进出口都受影响,手里握着钞票远不如囤积物资来的划算,至于大家听不听,做不做,那就是各人的造化了。
“要阿拉讲,舞照跳,马照跑,日本人来了也得依仗着上海,还能把上海打烂不成?”白先生又说话了,这回所有人都点头,连刚进门的赵殿元和杨蔻蔻也不例外。
难得有和邻居们交流的机会,赵殿元将沙逊大厦上看到的一幕讲给大家,听到日本人军力庞大,再联想到几年前国军在淞沪一线损兵折将的惨状,邻居们无不哀叹,上海是安全的,可其他地方呢,可整个中国呢。
大伙儿聊了一阵,意兴阑珊,各自回屋,只有周阿大回身推门推不开,敲了两下没有回应,便讪讪的下楼出门去了。
中午连灶披间都冷清得很,好像日本人和英美开战影响了大家的胃口一般,白先生和梅英倒无所谓,吃了午饭去赌场耍,在小白的撺掇下,梅英觉得在屋里和太太们打几毛钱的麻将太过没趣,沪西到处都是彻夜经营的赌场,耍起来才真叫过瘾。
上了专业赌台,方显英雄本色,梅英手气好的不得了,一连和了几把,面前筹码堆成山,白先生怂恿她把赌注押多一点,全押上,梅英正在犹豫,忽然进来四个汉子,面目不善,目光扫视一周,坐到了梅英这张赌台前,二话不说,掏出沉甸甸的手枪拍在台子上。
梅英胆小,吓得花容失色,两腿发软,手捂着胸口走也不敢走,求援的目光看向小白,白先生倒有几分机灵劲,看得出对方不是冲自己来的,这架势分明是来敲赌场竹杠的。
“先生,侬想哪能?”赌场管事的片刻就到了,横眉立目质问,这年头枪不算什么,赌场里配枪的保镖比街面上的巡捕还多。
“侬讲哪能?”那汉子一副滚刀肉的嘴脸,他就是被吴伯鸿打了一记耳光的阿宝,刚从巡捕房释放出来,日本人今天开进公共租界,阿宝兴奋莫名,从此整个上海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他的身份不得水涨船高,去赌场找点麻烦,敲个竹杠,弄点钞票解解晦气。
阿宝不傻,沪西的赌场烟馆都是大有来头的,没有76号或者日本宪兵队的背景谁敢做这个生意,他特意寻的一家小赌场,听说后台不是那么硬,再说自己胃口也不大,随便弄几十上百块就满足。
一帮彪形大汉从天而降,一眨眼的功夫就把他们拿下了,四个人重演昨天的一幕,跪在地上垂头丧气。
阿宝亮出身份,阿拉们是沪西警察分局的便衣侦缉,不看僧面看佛面,可人家只是嗤笑,一把雪亮的匕首丢到阿宝面前,让他给他的小兄弟们打个样。
道上规矩,犯了错就要认罚,阿宝是在场面上混过的,懂得这还是敬酒,不吃敬酒就要吃罚酒了,什么沪西警察分局便衣侦缉,在人家眼里狗屁都不是,统统丢进黄浦江汆馄饨,总之这回是踢到铁板了,阿宝也够光棍,拿起匕首连句场面话都不说,直接往大腿上攮,一刀下去再一刀,这个名堂叫做三刀六洞,玩得好的只伤肉不伤筋骨血管,玩得不好的话,当场就交代了。
第一刀下去,阿宝脸色蜡黄,豆大的汗珠滚落,他抽刀,用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刀柄上,不这样就没办法再次攮下去。
“够了。”一个声音传来,叫停了第二刀,一双深咖色雕花布洛克皮鞋踱到阿宝面前,厚厚一叠钞票丢过来:“拿去看医生。”
阿宝丢刀,抱拳:“谢不杀之恩!”
一张名片递到他鼻子底下:“看你是条汉子,以后有什么事体,提阿拉的名字。”
阿宝用沾满血的手接过名片,他不识字,还是旁人提醒他,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潘先生。
“谢潘先生!”阿宝明白这一刀没白扎,虽然伤了一条腿,但也抱住了大粗腿。
梅英和小白全程目睹了这血腥又江湖的一幕,惊的嘴巴都合不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