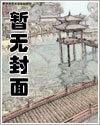新娘子愣愣的,喜娘说什么都没反应,而新郎官面无表情,喜娘说一句,他才动一下挑开新娘的盖头时,那容光将整个陋室都照得恍如仙境了,喜娘甚至都忘了词儿,但新郎官却依旧没反应。
回过神来的喜娘赶紧道:“请新郎官为娘子挑帘。”
这却是本朝特有的成亲习俗。新娘不仅要头顶红盖头,而且还得戴垂着面帘的花冠。从新娘家中出来、上轿再到拜堂成亲,新娘都只需要戴面帘就行了,方便她能看得清路,不至于跌跟斗。
因为以前戴盖头出过不少事儿,有新娘在跨马鞍时绊住了,脑门儿冲下直接摔成傻子的,还有新娘出门下阶梯的时候没看着路直接摔死的。后来就渐渐演变成入洞房之后才戴盖头了。
如今大红盖头下还有面帘,所以就多了一道程序,“挑帘”。
原本这一幕是最好看的,新郎、新娘侧坐对视,新郎官柔情细致地为新娘拨开眼前的面帘,轻轻地挂在两侧,然后两人就能毫无阻碍地含情脉脉地对视了。
但眼前这对新人却非如此,新郎官为新娘子拨开面帘时,动作干净利落,挑开后直接转过了头没再看新娘子。
喜娘刚才隔着面帘看新娘已经是失了神,这会儿再看到新娘子的脸就只剩惊艳、惊艳再惊艳了。
都说华宁县主是京城第一美人,甚至是天下第一美人,她以往也见过这位县主,但此刻见她盛装静坐,依旧再次惊艳了。
长孙愉愉的眉心一朵芙蓉花钿,花蕊贴着一枚湛红如火的红宝石,将一张脸衬托得笔墨难描,女娲难造。
喜烛的光映在她脸上,仿佛都被比得暗淡了,那光晕一点一点在她脸上细致地搜寻,却也没寻出任何瑕疵来。
这样的美人儿,别说男人见了,就是她们女人见了都心生喜爱,恨不能看了又看。这般美貌早就已经脱离了让人嫉妒的界限了,只余折服和心叹。
偏那新郎官依旧无动于衷。
喜娘想着眼前这位可是晋阳公主的独女,晋阳公主又是出了名的豪富,娶得这样美貌的娘子,还富可敌国,新郎都是这副表情,那些传闻岂非都是真的?新娘子早已失贞?
喜娘胡思乱想归胡思乱想,但嘴里却还得继续说着喜庆的话。只不过两位新人的冷脸,让喜娘的吉庆话说得都没那么激0情了。
陆行神色冷峻,看也不看长孙愉愉,后者对他的态度并没多意外,他本就避她如毒蝎的。她们这桩亲事,长孙愉愉叹息,都是她娘亲一厢情愿强扭来的,也不知会是个什么光景。
不过陆行嫌弃她正好,长孙愉愉在心里撇嘴,正好她可以提出让他去别的屋睡觉的事儿,想来他肯定不会拒绝。今后他们就各管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在长辈面前就一起装装样子好了。
热闹过后,喜房里总算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长孙愉愉以及莲果、文竹两名侍女了。冬柚和负责账本的乐桃都留在了宁园,实在是陆家住不下。莲果和文竹也只能两人挤在一个房间里。
静悄悄的喜房内,长孙愉愉呆呆地坐在床上,木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膝盖,一动不动。
莲果和文竹对视一眼,莲果上前一步低声道:“县主,记打早晨起你就没吃东西,我去厨房叫准备吃食吧,文竹伺候你更衣。”
“不想吃,先伺候我更衣、沐浴。”长孙愉愉声音有气无力地道。
文竹麻利地帮长孙愉愉歇下花冠,又伺候她换了嫁衣,莲果则去厨房叫热水去了。
整个过程长孙愉愉都没再说话,一直到起身去净室时。
才走到净室门口,长孙愉愉就再不肯挪动脚步,文竹诧异地在后面等了十息,也等不到长孙愉愉的动静,往前探头一看,才发现她家县主早已是泪流满面。
“县主。”文竹有些无措地唤了一声。
长孙愉愉再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返身扑向床上,将头埋在大红的鸳鸯戏水被子里就开始大声地哭了起来。
文竹忙不迭地跟上去,在旁边劝道:“县主,可不兴在洞房里哭呢,会不吉利。”
长孙愉愉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吉利不吉利,她觉得嫁给陆行就是最不吉利的事情。瞧她自己一个谎言把她害成了什么样子。她此刻恨不能在晋阳公主跟前大声地哭喊,她根本就不喜欢陆行,她都是骗人的。
莲果一进屋就听到长孙愉愉的哭声了,无声地拿眼神询问文竹,文竹只摇了摇头,又指了指净室的方向。
莲果悄声地往净室走去,但见那净室都及不上宁园长孙愉愉屋里净室里那池子的大小。长孙愉愉的池子那是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都蓄着冒着热气的水的,而这净室里却只有一只孤零零的大瓷缸。
模样也是奇怪,半埋在地下只露出个边沿来。
地砖?当然是没有地砖的,只是用青石板铺就,显得十分灰暗。而长孙愉愉的净室里那池子却是汉白玉雕就的,隔断都是用的镂空青玉板,华丽得仿佛龙宫。
天差地别的净室,仿佛也预示着她婚前婚后天差地别的日子,长孙愉愉只看了一眼就悲从中来,再无法抑制对未来的惶恐不安以及绝——望——
这世上有哪个女儿家没憧憬过未来和良人一起的日子的?长孙愉愉虽然不想嫁人,但豆蔻年华之后偶尔也会思量。如今看到陆行那副做派,她一颗心比寒冬腊月泡在冰水里还冷。
莲果和文竹是怎么劝也劝不住长孙愉愉的哭声,到最后只能任由她哭。
文竹坐在长孙愉愉的身后替她理着背脊,莲果则低声道:“县主,其实净室也没那么差。奴婢刚才去厨房了,那边专门有一个烧水的灶,连着陶瓷管子,净室这边用水,那边儿烧了水立即就能通过管子送过来,都不用人去抬水的。”
文竹听了侧头看了看莲果,莲果朝她点了点头,又往净室去看,再回来时道:“县主,净室的瓷缸里已经蓄满水了,奴婢伺候你沐浴吧。要是眼睛哭肿了,明儿认亲时可怎么说?”
哭归哭,但澡却还是要洗的,长孙愉愉由着莲果两人扶着进了净室,一看到那简陋的模样,眼泪就又涌了出来,坐在浴盆里继续哭。
莲果和文竹无奈,小心地伺候起长孙愉愉,格外用心地给她擦拭身上的水,还有就是沐浴后上香膏、推拿、梳头等等。
先是用香膏裹住脚跟、手肘,再拿云棉布裹了,那棉布是在熏笼上烤着的,相当于是热敷了。再接着文竹用特制的紫檀梳拿着长孙愉愉记340;头发细细地、轻轻地梳着,还顺带给她用特制的大梳子刮头皮,莲果则是熟练地替长孙愉愉揉按其他抹了香膏的地方,如手指等等。
这一番伺候下来就是再坏的心情也能平缓。
长孙愉愉也不再哭泣,只蜷缩在床上,文竹转身倒茶的功夫,她就睡着了。
一张小脸红扑扑地裹在大红被子里,越发显得肤白如雪,唇若涂丹,长长的睫毛覆盖下来,仿佛一对黑漆小扇子。
红、白、黑三色对比到了极致,极致到了艳丽的地步,陆行回屋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张脸。
文竹忙地朝陆行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朝睡熟的长孙愉愉努了努嘴,提醒陆行。
陆行点了点头,从衣橱里拿了自己的衣裳直接进了净室。他很有自知之明,没想过能得着莲果和文竹的伺候。
陆行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时,莲果和文竹一个守在床尾一个守在床头看着长孙愉愉,假装在做针线却是半天一针都没下。
陆行从小就没让侍女伺候过,更是不习惯这屋里骤然多出三个女人的情形,愣了片刻拿了棉巾直接出了门。
莲果和文竹对视一眼,都没来由地松了口气。
躲在角落看热闹的傅婆见陆行从洞房里出来,不由得迎了上去,“这是咋的?被赶出来了?“
这语气听着可有些幸灾乐祸,陆行朝傅婆笑了笑,兀自在廊下用棉布擦起头发来。等着听洞房壁脚的青老啥也没等着只能钻了出来。
陆行感觉头发干得差不多了,这才在青老和傅婆的瞩目下重新推开了洞房门。
莲果和文竹齐齐地朝陆行望去,陆行将棉帕往旁边放下,“你们也去歇着吧。“
莲果和文竹都没动。
三个人就这么僵着。
最后还是文竹扯了扯莲果的衣袖,两人才慢腾腾地出了门。毕竟这是洞房花烛夜,谁也没道理拦着新郎圆房,她们两个丫头更是不敢。
只是两人出了门也不敢去歇着,就桩子一样地守在门边儿,打算一听到什么不好的动静儿或者呼救声,两人就往里冲。
但等了好半晌,屋子里也没任何动静儿,以至于院子里四个无聊的人都开始打起了哈欠。
而红烛高照的屋子里,陆行已经上了床,仰躺在长孙愉愉身边,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动手动脚,他也打了个哈欠准备睡觉。
可也只是准备而已。
一辈子没亲近过女人的年轻男子,好容易成了亲,洞房花烛夜不干点儿什么实在过不去。
偏陆行就那么静静地闭着眼睛。
长孙愉愉已经彻底睡熟,毕竟是个小姑娘,哪怕心里一直惦记着不许陆行圆房这件事,但她愣是没抵御住瞌睡虫的威力,就这么毫不设防地呈现在了人面前。
到最后约莫过了一个时辰,陆行长长地吐了口气,翻身背对着长孙愉愉打算认真睡觉。
然则身后的人却似乎有了动静儿。
陆行的腰上搭上了一条腿,一张脸也搁他背上蹭,手四处摸着,在寻找最温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