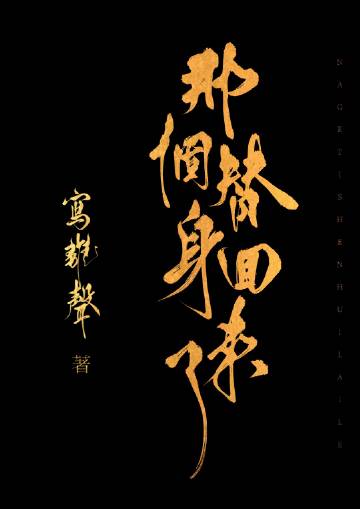许、章两位长老面面相觑,??不明白审问一个刚入门的小弟子,为何会惊动玄渊神君驾。
而那执法堂主已跪倒在地。
冷嫣然猜不出谢爻此举何意。
她对自己用的傀儡丝并非寻常傀儡丝,不及头发丝的万分之一,??除非承袭偃师宗傀儡术的奥秘,??否则修为再高探查不出来。
其实要分辨是否傀儡身,??最简单的方法是一刀杀死,普通傀儡会现出原型,而偃师宗的傀儡则会为蝴蝶纷飞。
另一种方法则是将极细的一脉剑气入体内,??试探躯壳的反应——傀儡的反应与真有着微妙的差别,??要用这种方法,此的修为必须极高。
谢爻在与她对剑时便用这样的手段,然而冷嫣的傀儡丝系在神魂上,??这点细微差别被她抹去了,即便是他分辨不出来。
但是即便他查她的脉,完没必要将此说出来,??没理由亲自赶来。
难道是要放长线钓鱼?
正思忖着,谢爻已走进执法堂中,??向两位长老一揖:“请教两位长老,私设刑堂,??向无辜弟施搜魂术,??按门规该当如何论处?”
冷嫣看着这个熟悉的男,他的半个隐藏在黑暗中,??鲛灯清冷的光晕照出他小半张脸,依旧清隽出尘,宛如谪仙,他说出的话又是如此义凛然、义正言辞。
然而没有什么比这句话从这个嘴里说出来。
冷嫣乎要出声来,她勉强忍住,??意憋在心里,胸腔都有些隐隐作痛。
许、章两却有些惴惴不安,昆仑君地位超然,凌驾于掌门与长老之上,只是不理俗务而已,谢爻平素在他们面前执弟子礼,不敬他们是长辈,若较真起来,是以按门规处罚他们的。
受罚小,但这脸面往哪里搁?
章明远忐忑道:“按门规该受四十鞭。”
谢爻扫了眼跪在地上的执法堂主:“那便请吴堂主依律领罚。”
章明远略微松了一口气,他总算他顾两颜面,只是处罚一个堂主以儆效尤。
许青文的脸『色』却不好看,那吴堂主是她座下意弟子,谢爻这样一句话便治了他的罪,不啻于一掌掴在她脸上。
谢爻却不管他们怎么想,扫了眼挂在墙上的神鞭,对许长老道:“吴堂主是许长老高足,便由许长老执法吧。”
许青文心一沉,若是让章明远行刑,他下手轻一点无厚非,但由她惩罚自己弟子,轻了便有徇私包庇之嫌。
神君既已发话,她只能硬着头皮从墙上摘下神鞭,照着亲传弟子的脊背,结结实实地了下去。
受完四十鞭,吴堂主衣衫尽湿,要维持跪姿已十分勉强,但还是稽首称谢:“谢神君教诲,谢师尊降罚。”
许青文心疼不已,忙唤来道僮将他扶回住处,又传音命送去上好伤『药』。
谢爻程面无表情地看着,连眉头未动一下。
观罢刑,他向章、许二点了点头,便即转身出了执法堂。
回到玄冰窟中,谢爻看着沉重的石门降下,隔绝了他和外面的世界,方才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坐下来,他的中衣后背已被冷汗浸透。
神鞭抽在皮肉上的声音仍然在他耳边回响,一个单薄纤秀的身影从不冻池中缓缓爬出来,双臂交叠,趴在池边上,精巧的下颌搁在手背上,幽深漆黑的眼眸定定地望着他,湿发裹着肩头,像个精魅,眼下的胭脂痣宛如宝石。
谢爻已无力与脉中的阴邪之气对抗,任由那幻象占据他的心神,吞噬他残存的理智。
“师尊,你觉巴巴地跑去救那凡女孩能补偿我么?能让你的良心稍安么?”少女的声音在洞窟中回『荡』,像幽魂般空洞,“你真会自欺欺。”
她轻轻叹了口气:“你亲手杀了我,难道你忘了?”
她俏皮地一,『露』出一颗略微有些歪的小虎牙:“师尊,把心意相信你的无辜弟子剖灵府、割元神,依门规该当如何处置?”
谢爻颤抖起来,齿关咯咯作响。
少女发出一串没心没肺的轻,双臂轻轻一撑,只听水声哗然,她已从冰池中站起,湿透的衣衫贴在身上。
谢爻用尽浑身的力气,将背紧紧抵在墙上,粗糙的冰岩很快便将他的后背磨出了血,但他毫无知觉。
少女却已走到他面前,掀开湿透的衣襟。
谢爻下意识地闭上双眼。
“没用的,师尊,”少女道,“我在你心里,闭上眼睛你看不见了么?”
然,闭上眼睛毫无用处,眼前是雪浪一般的白。
少女纤细的手指在腹上竖着划了一道,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还记你怎么剖开我的灵府么?”少女把手伸进伤口,拽出一团似雾又似云的东西,捧到谢爻面前。
谢爻不想看,却不不看,那团雾气般的东西是个抱着膝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少女,五官依稀辨。
“这是我的元神。”少女说着,对着手中的东西轻轻一吹,那元神瞬间碎裂成了无数片,闪着微光,像云母碾成的碎屑。
谢爻行气将感官尽数封闭,但渴望的黑暗和寂静并未来临,她说的没错,她在他心里。
少女在他身边跪坐下来,轻轻地捧起他的脸,眼中满是疼惜和恋慕:“没关系,阿爻哥哥,你还有我啊……”
这句话仿佛一根尖锥刺进谢爻神魂中,将他捅了个对穿。
温软的唇已覆了上来,馥郁的兰花香迅速弥漫,令他欲窒息,谢爻想将她推开,他的手却穿了那具温热柔软的身体,她黏在他身上,犹如跗骨之蛆,犹如洗刷不掉的罪孽。
……
谢爻走后,许青文量着苏剑翘,他直到此时仍不明白谢爻为何小题做。
少女规规矩矩地跪着,身形单薄,在微弱的光线中辨不清面目,乍一看莫名有些熟悉。
当她终于想明白那股熟悉的感觉从何而来时,心头不觉一震。
她本来与这凡弟子并无私怨,审问她只是出自公心,搜查脉魂魄固然会伤她根本,但为了宗门安危是情非已,她已算好,若这弟子无辜,她便从自己私库中拨出上好灵『药』给她养伤。
是此时想起另一个少女,她心里却涌出许多黏黏腻腻的东西来,像一团团污泥堵在她心口,既烦恶,又夹杂着些恐惧。
对勾起这些情绪的苏剑翘,她平白生出了许多恶感,一半来自她的良心,另一半则来自她对郗子兰的回护——这么多年来,她其实明白谢爻的心结在哪里。
但她不敢再去触谢爻的逆鳞,只是挥挥手,向苏剑翘道:“你退下吧。”
许青文回到仓宫,去探望了一下受罚的吴堂主,然后去主殿中坐了一会儿。
仓宫的宫殿按一峰之主的规格建造,但许青文起居都在偏殿中,主殿正堂中放了妘素心的排位,寝殿里放着妘素心的旧物——郗子兰长后重新修葺了玄委宫的主殿,一应陈设都换了一遍。
许青文不忍见旧主用的器物堆在库房中不见天日,索『性』令搬到空置的正殿中,按照主生前的样子布置起来。
只要闲,她便会来这里坐坐,拂拭拂拭灰尘,有时候一个恍惚,她会生出种小姐还活着的错觉。
她将户牖开,让山风和清气灌满寝殿,把瓶中略微有些萎蔫的桃花换成刚采摘的山花,又仔细地将一件件器物上的浮灰擦拭干净。
她擦很慢,每当心『乱』时,这么做以帮她静下心来。
做完这一切,外头已响起鸟雀归巢的啁啾声,她重新阖上窗户,残阳透窗纸照在寝殿中,在妘素心的妆台上流连不去。
日暮时分总是格外令伤怀,许青文不忍再多看一眼,将灯台里的灯油倒空,换上新的,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在这时,她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细碎的铃声,蓦地一怔。
与寻常铃声不同,这串铃音高低起伏,断断续续地连缀成一首简单的曲子,清微界每个襁褓中的婴孩乎都听母亲哼唱这首《昆仑谣》。
昆仑金铸成的铃铛以发出天然的乐音,有将之谱成歌谣,据说乐音里带了羲和神的祝福,除邪祟,避灾殃,保佑孩子一世平安。
但此种铃铛的铸造之法早已绝迹,传世的铃铛极少,只有一些古老的世家代代相传。
妘家珍藏了一串,妘素心小时候戴,女儿出生后又戴到了她手上……
是那串铃铛去哪里了呢?
许青文坐在榻上冥思苦想,她记小主刚出生时妘素心便亲手替她戴上了铃铛,不知什么时候那串铃铛便不见了。
她一想起妘素心仙逝时的情形便觉心如刀绞,这些年来不愿仔细回想,此时竭力回忆,却发现记忆上仿佛蒙着一层雾,只依稀记主临终前的谆谆叮嘱,一旦深想,却像喝了酒似的头脑昏沉。
她的记『性』一向很好,是主逝世这么重要的,这么多年来她却没有察觉不对劲,这显然不正常。
铃铛声由断续变连贯,由缓慢变急促,许青文只觉脑海中的『迷』雾慢慢散去,她终于想起妘素心临终前的种种不同寻常之举。
铃声戛然而止,随即“铛啷”一声,一串金铃从房梁上落下来,掉在她脚边。
妘素心捡起一看,那铃铛由红绳串起,正适合婴儿手腕,但铃铛却只是普通的紫阳金铸成。
她晃了晃,铃声细碎,并不是《昆仑谣》。
那么方才她听到的昆仑遥又是哪里来的?这串铃铛又是从哪里来的?
她忽然想起曾听主说起,修为和阵法造诣极高的以通布阵『迷』『惑』阵中的心智,甚至通唤起心底的情感,来模糊甚至篡改的记忆。
她一直以为这只是传说,直到这串破邪的铃音拨开『迷』障,将记忆的封印撬开一角。
妘老掌门便是阵法家,但连他做不到,不他有个青出于蓝的弟子,于阵法一道比师父钻研深——郗云阳。
她知道自己应该将这种种古怪立即告诉夏侯俨和章明远,但她刚抬起手准备捏诀,又改了主意。
她太了解妘素心的一颦一,她临终前对女儿的态度实在太古怪,让她生出了一个怕的念头,单是想一想便叫她心惊胆寒。
如……她必须先悄悄地查清楚真相。
天留宫中,冷嫣晃了晃手中的昆仑铃,铃铛发出悦耳的乐音。
昆仑金的铃铛传世极少,为数不多的串都在世家手中,若非姬若耶供奉给若木的箱珍宝中刚好有一串,她一时半会儿不知上哪儿去找,只能想别的法子提醒许青文。
她将铃铛还给若木,心里有些不舍,这铃音莫名让她感到安心和温暖,不昆仑金铃本是吉祥之物,唤起宁谧温馨之感是理当然。
若木道:“喜欢便留着。”
冷嫣道:“我用不上,你以留着当传家宝。”
若木将那绳子拆了,从乾坤袋中取出一条赤金丝编成的软绳换上,顺手便系到了雪狼的脖颈上。
祂撩了撩眼皮:“你不要给狗。”
冷嫣:“……”
雪狼显然觉这叮铃作响的东西有损它的威仪,千方百计要将它扒下来,奈何那绳子施了咒,它的爪子又不够灵便,挣扎了半晌,直把自己折腾气喘吁吁,总算认命地趴了下来。
若木道:“你什么时候猜到许青文的记忆被动了手脚?”
冷嫣道:“听石红『药』说完我便开始怀疑。”
她揪了揪雪狼的耳朵:“许青文是妘素心最亲近的侍女,章明远对妘素心痴心一片,谢爻视师母为母,不管哪一个都比谢汋了解她,连谢汋一个小童都能看出来不对劲,他们怎么能一无觉?”
她顿了顿道:“偃师宗的术法中有一脉来自上古昆仑一族的巫蛊之术,其中便有『惑』心智的术法,和偃师宗同源的重玄很能有类似的术法,但这种术法不能平白起效,在悲喜之际最能趁虚而入。
“谢汋生来薄情,受的影响反而微乎其微,才将那些记那么清楚。还有那串昆仑铃,摘走那串昆仑铃的未必是妘素心,察觉女儿被道侣调换,一定是灭顶的击,这种情况下她未必有心思注意一串小小的铃铛。昆仑金的铃音有辟邪除祟、清心明志之效,若有铃铛在,施术便没那么顺利了。”
她忽然发觉自己竟说了那么多话,蓦地怔了怔。
她习惯了踽踽独行,不知不觉中,身旁多了一个,她开始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祂,渐至无话不说。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不清楚,像说不清楚封冻的河流什么时候开始融。
她只知道这绝不是个好兆头,她一个的复仇路是不该有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