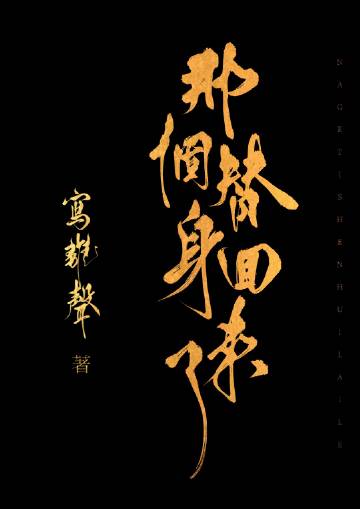夏侯俨送了郗子兰一棵洞光珠树,??亦是难得的珍宝。
接着内门其余诸人、小辈弟子都有贺礼相赠,各大宗门与世家也送来了贺礼——虽凌霄恒和谢汋出事,重玄第一仙门的地位并未撼动,??其它宗门看重玄的笑话,??却不与重玄撕破脸。
郗子兰将每样礼物接过观览,??后交给仙侍放到一旁,不一儿她座旁便堆得好似小山一般。
每年生辰她都收到许多贺礼,拣几样合心意的收入小库,??其余的便登记造册送到大库房里,??偶尔拿两件出来赏人,其余的便放上几百年积灰。
眼看着最后几件贺礼陆续送到郗子兰眼前,接着就该由众人依次上前祝酒了。
姬殷向冷嫣:“一儿我与你冯师叔他一起祝酒,??你跟着师兄师姐。”
冷嫣点头应承,她自不喜欢向郗子兰敬酒拜寿,但为免惹人注意,??也只能忍一时之不快。
就在这时,忽有两个仙侍抬了一口巧夺天工的金银平脱黑檀木箱来。
郗子兰瞥了眼赞,??见他已将礼单卷起来收好,不由诧异:“怎么还有贺礼,??这是谁送来的?”
那两个仙侍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开宴前这些生辰礼都存放在殿后,只等着筵席上依次进献,??他看见这口箱子,便抬了过来。
其中一人如实答了,郗子兰看了看精巧的箱子,不疑有他:“大约是造册时遗漏了,抬上前来吧。”
仙侍将箱子放到几案上,??便要打开箱子上锁扣。
就在这时,谢爻忽:“慢着。”
郗子兰:“怎么了,阿爻哥哥?”
不等谢爻说么,忽听“喀喀”数声,那看起来坚固无比的檀木箱忽四分五裂,“哗啦”一声,猩红『液』体泼了满案,众人随即闻到一股冲天的血腥气——那口箱子里竟装满了血。
鲜血中有么黑黢黢的东西在蠕动,有人惊呼:“那是么!”
话音未落,那东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起,竟直直地照着郗子兰的面门扑。
她哪里来得及反应,等抬抓,那东西已经贴在了她脸上。郗子兰只觉触冰凉滑腻,蓦地意识到那是么。
是蛇!
她尖叫了一声,立即松开,几乎昏厥过,蛇张开血口,『露』出毒牙,眼看着就要一口咬下。
说时迟那时快,一剑光闪过,那条蛇被斩为两半。
“啪”一声,蛇从她脸上掉落下来,半截掉在地上,半截掉进她面前的酒杯里,蛇尾挂在杯沿上,还在扭动。
郗子兰再也忍不住,捂着嘴吐了出来。
幸而她方才只顾着偷觑谢爻,只饮了那杯千日酒,吐完便只是抚着心口干呕。
冷嫣认出那蛇的来历,向若木传音:“是你做的?”
若木“嗯”了一声,痛快地承认了:“么东西也配让人祝酒拜首。”
冷嫣心头蓦地涌出一股暖意。
连她都不在乎的事,却有人提前替她想到了。
或许是冷得久了,那暖意几乎让她觉得有些灼烫,不觉眼眶微酸。
良久,她轻轻:“多谢。”
若木轻哼了一声:“本座只是看她不顺眼。”
祂顿了顿又:“一点小事别总是谢来谢,烦得很。”
谢爻看着那条蛇,脸『色』阴沉得能滴下水来。
郗子兰不认识这蛇,他和夏侯俨、两位长老却都是认识的。
这是伴着血菩提而生的棘蛇,平日盘在树下宛如树根,有人采摘那邪物时便暴起伤人,若是再迟刹那,郗子兰这张脸至一两个月不能见人。
他本应及时拔剑的,但认出那蛇之后,他不由自主地瞥了苏剑翘一眼,便是因了这一眼,他的剑便晚了刹那。
不过也是因为这一眼,他从她眼中看到了货真价实的惊诧——所以她并不知情。
不知怎的,他释之余,又有些淡淡的失望。
其余三人也都认出那是何物,其他两人尚能维持镇定,许青已是脸『色』灰青,浑身战栗,简直已不似活人。
“那箱子里还有东西!”有个眼尖的弟子惊叫。
箱子里的血已经淌干了,『露』出底下婴儿拳头大的一团。
谢爻目光一触及它便知这是么。三百多年前他也曾看见过一颗,那个女孩为了他不顾危险潜入禁地,拼着被毒蛇咬伤,摘了来送给他。
他还记得她将血菩提捧在心里,全不知那是给她带来噬心之痛的邪物。
谢爻的心口又开始抽痛起来,或许从那一夜开始,在他胸腔里跳动的也已不再是心脏。
他捏了个诀,真火燃起,很快将断蛇和血菩提烧成灰烬。
但一地的鲜血还在。
郗子兰终于止住了翻江倒海的恶心,谢爻轻揽她的肩头,她便趁势躲在谢爻怀里抽泣起来。
最初的哗之后,弟子都自觉地闭上了嘴,一个个大气也不敢喘一口,鸦雀无声的大殿中只有郗子兰的啜泣声。
弟子不知那团东西是么,也认不出那是么品种的蛇,但生辰宴上见血,谁都知有多不吉利。
更可怕的是堂堂羲和传人被一条蛇吓得失声痛哭,这或许比蛇和血更令弟子悚不安。
本来夏侯俨等人想借这场生辰宴稳定人心,没想到适得其反。
更难以索解的是这箱东西究竟是怎么混进来的——自从偃师宗寻衅开始,宗门上下戒备森严,护宗大阵之外又设了重重禁制,可以说连一只飞蝇都钻不进来。
夏侯俨皱着眉看了一眼郗子兰,向谢爻:“元君受了惊,先回歇息吧。”
谢爻颔首,扶起郗子兰:“我送你回玄委宫。”
就在这时,许青却上前:“此事蹊跷,还请君留下来与掌门一起主持大局,元君由老身护送即可。”
郗子兰的身子一僵,她心里自是一万个不情愿,但谢爻已接口:“有劳许长老。”
许长老便即扶着她快步向外走。
刚走出几步,身后有人跟了上来,许青转过头一看,却是冷耀祖。
冷耀祖在西华苑这段日子显过得不太好,形容惨悴了不,他好不容易一朝翻身,当要着意表现,师尊受惊这样的机怎么能错过?
他快步跟上前,如以前一样吩咐随从赶紧备车驾,片刻便将一应细节安排得周详妥帖。
却不知此举正合许青的意,本来她还得找个借口将冷耀祖召玄委宫,正好省了这麻烦。
郗子兰与许长老上了车,心下有些奇怪,换平日,她遭了这么大的罪,许青这儿一定拉着她的嘘寒问暖,可她却么都没说,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许姨,你怎么了?”郗子兰试探着问。
许长老这才回过来:“无事。子兰还好吧?”
郗子兰:“幸好阿爻哥哥那一剑及时,只是唬了一跳,许姨知我怕蛇的。”
许长老心事重重地点了点头,便又陷入了沉默。
不一儿,凤车停在了玄委宫前,许青方才感觉这一路有一百年那么长,可到了殿中,她又惊觉图穷匕见之时来得这样早。
郗子兰想叫冷耀祖退下,许长老却:“等一等。”
郗子兰纳闷:“许姨,你找耀祖有么事么?”
许长老拔出腰间短匕,对冷耀祖:“借你三滴血一用。”
冷耀祖疑『惑』地看向郗子兰,郗子兰也莫名其妙:“许姨……”
许长老脸『色』已成了铁灰,在灯火中看起来犹如僵尸,她打断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照我说的做。”
郗子兰对冷耀祖使了个眼『色』,冷耀祖只得乖乖伸出。
许长老用匕首划破他指尖,取了三滴血在琉璃瓶中,后:“你殿外等候,我不叫你不许进殿中一步。”
郗子兰:“吧。”
待冷耀祖退出殿外,郗子兰方才:“许姨你怎么了?别吓子兰啊……”
许长老:“冒犯小姐。”
话音甫落,她嘴唇轻动,默念口诀,琉璃瓶中的三滴血却只一动不动。
许青一连试了数次,那三滴血依旧纹丝不动。
许青叫来两个仙侍,问:“你两人是亲姊妹对不对?”
仙侍答是,许青故技重施,割破姐姐的指放了三滴血,施了同样的咒术,那三滴血立即向妹妹飞,没入她的眉心不见了踪影。
许青面如灰,后退两步,跌坐在榻上。
郗子兰叫她这模样吓得不轻,连身干净衣裳都没顾上换:“许姨,这到底是么意思?”
许青挥屏退了侍从,这才抬起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她,声音嘶哑得好像用沙砾磨过:“你这具躯壳……和冷耀祖不是同一血脉。”
郗子兰隐隐察觉到了么,但不愿深想,勉强微笑:“许姨今日到底怎么了,你说的话子兰怎么听不明白?”
许青不知从何说起,想了想,颤声:“你的身世可能有问题。”
郗子兰骇:“么?”
她不知怎的想起沈留夷的眉眼,还有她眼角那颗细痣,曾经一闪即逝的那个可怕念头在心里杂草一样疯狂滋长。
不可能的,她安慰自己,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许青见她冷『色』惨白,心中又生出不忍,缓和了声气:“子兰,你可能不是小姐的骨肉,而是冷家的女儿……其中可能有么玄机。但究竟是不是,还要请君用法阵提出你和耀祖的魂魄来验一验才能确知。”
荒诞的噩梦像头巨兽吞噬现实。
郗子兰只觉耳边轰地一声响,随着许青的一句话,她琉璃天宫般光华璀璨的世界好像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