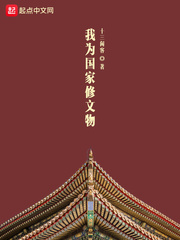向南一边回想着项元汴充满传奇色彩的“富二代”生涯,一边慢慢来到长安博物馆的西大门停车场的位置。
还没等多久,朱熙就亲自开着一辆蓝色的保时捷,赶到了这里。
向南上车之后,朱熙将车子调了一个头,一脚踩下油门,车子就又蹿了出去,很快就汇入了滚滚车流之中。
坐在副驾驶座上,向南看了看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搭在车窗上的朱熙,开门见山地问道:
“项元汴的画在哪儿?”
“现在就要看吗?这么着急?”
朱熙有些意外地扭头看了向南一眼,又很快转了回去,笑道,
“那画不在车上,在朋友那儿,我现在就是往那边去。”
说着,他又解释了一句,“这画并不是我的,而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前几天刚刚从一个小型拍卖会上拍得了这幅画,挂在上才欣赏了没两天,结果被他三四岁的女儿扯了一下,给扯烂了。”
“我今天到他那儿有点事,刚好看到那幅古画,见他也没拿去修复,所以就给你打了个电话,看看你有没有兴趣过来看看。”
说到这里,朱熙又瞄了向南一眼,开玩笑似的说道,“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太热心了,你不会怪我给你找事吧?”
“不会。”
向南笑了一下,给我找事?这种事,你给我多找一些来,我保证不怪你。
“对了,这幅画画的是什么?”
“唔,我没细看……”
朱熙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也没有,很理直气壮地说道,“我爷爷是收藏家,我又不是!”
我只是一个“专职富三代”而已,会花钱就可以了,干嘛要懂那么多?
“……”
向南撇了撇嘴,都是富家子弟,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人家项元汴也是豪族子弟,比你家有钱多了,家里的收藏品都能顶半个故宫,可人家也没像你这样只会花钱,啥都不懂啊。
且不说项元汴鉴赏能力超群,无人能比,光是书法、绘画,人家那也是无师自通的。
就连皇帝都亲自下诏请他出来做官,人家不屑去而已。
想归想,向南可没打算将这话说出来。
一是他和朱熙还没熟悉到这个份上,二是人家家里的长辈都不管,他操的什么心?
有那个闲心,还不如多修复几幅古字画,几件古陶瓷呢,没看到博物馆的库房里堆得满满的文物,都没人去打理吗?
朱熙当然不会知道向南在想些什么。
他的车技十分娴熟,在长安市区的大街小巷里转来转去,很快就开进了一个看着颇为高档的小区里,然后在一栋花园洋房前停了下来。
停好车之后,朱熙朝向南露齿一笑:“走吧,我带你去看看那幅画。”
说完,便率先上了楼梯,在前面带路,他一边往上走一边回头解释道,“这边的小洋房总共只有六层楼,都是不带电梯的,他就住三楼,很快就到了。”
向南笑了笑,爬几层楼算什么,他在金陵大学的宿舍都是在七楼的,一样没有电梯,大家不一样每天上上下下好几遍的。
尤其是轮到打开水的日子,一个人还要提四个大热水壶上楼呢,一口气上七楼的感觉,那才叫酸爽!
当然,这样的生活体验,估计朱熙是不会有的,他读大学时,不是回家里住,就是在外面租房住——呃,说不定大手一挥,在读书的城市里,买一套房子也不是不可能。
那胖子钱小勇就因为读了古玩鉴定专业,还专门在金陵开了一家古玩店呢。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向南和朱熙都是年轻人,腿脚快,三层楼没几步就到了,连大气都没喘一下。
此时,三楼楼梯左边的那扇防盗门已经大开,一位看起来比朱熙略显老成的男子,穿着一身居家服,站在门口看着两人,一脸热情地招呼道:
“欢迎,欢迎!”
说着,又对朱熙道,“朱熙,快请客人进去,我已经泡好茶了。”
朱熙跟这男子关系应该很好,在他家里也是相当随意,闻言便将向南领到客厅里的沙发上坐下,然后又走了出来,有些奇怪地低声问道,“刘哥,你还叫了其他人来?”
“没有啊!”
刘剑平一脸奇怪,似乎不明白朱熙为什么会这么问,他反问道,“你不是说请了个专家来?专家不是在后面没上来吗?”
“……”
朱熙一脸无语,他都忘了,当时看到那幅破画的时候,只跟刘剑平说了要帮他请个专家来帮忙修复,却没提这位专家实际上比他年纪还要小!
也难怪刘剑平会误以为,专家还在楼下没上来呢!
刘剑平也不傻,看到朱熙的表情后,也很快反应过来了,顿时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指着屋里正在悠闲地喝着茶的向南,低声问道:“他……就是那个专家?”
“嗯,他叫向南,国宝《千里江山图》就是他修复的。”
朱熙狠狠地点了点头,又补充了一句,“我爷爷亲口说的!”
刘剑平立刻就信了。
朱熙的爷爷是谁,那可是国内有名的大收藏家,他说的话,当然不会有假。
再说了,他骗谁也不可能骗自己的孙子啊。
“走走走,赶紧进去。”
刘剑平推了一把朱熙,低声道,“这么年轻就是专家,以后前途无量啊!我说,你小子可得跟人家打好关系,你们家那么多收藏,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有求到人家的时候。”
朱熙一边点头一边笑道:“刘哥你就放心吧,咱这交际能力还是可以的。”
“你就得了吧。”
刘剑平嗤笑一声,略有些嫌弃地说道,“别以为什么人都可以靠钱来维持关系,有些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你得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朱熙若有所思,难道专家就不喜欢钱?
刘剑平见状,拍了拍他的肩膀,便赶紧去招呼向南了。
“向专家,不好意思,刚刚有点事,怠慢了。”
刘剑平一到客厅,就笑着招呼道,“我叫刘剑平,是朱熙的老大哥了,以前两家住隔壁的时候,他光着屁股那会儿,就成天跟着我跑来跑去。”
这时候,朱熙也回过神来了,听了这话,立刻大声否认:“刘哥,你也就大我两岁,我光着屁股的时候,你也没多大吧?哪记得那么清?说不定咱俩是一起光屁股的!”
刘剑平笑呵呵的,也不反驳。
朱熙得意地笑了笑,跟向南介绍道:“刘哥是做建筑设计的,是我爸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尤其擅长设计中式建筑,拿过很多大奖的。”
向南这时候也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听完朱熙的介绍后,他跟刘剑平握了握手,脸上露出了程式化的笑容,淡淡地招呼了一声:
“久仰久仰!”
随后,也不等朱熙和刘剑平再说什么,直截了当地问道,“请问刘先生,能看看那幅损坏的古画吗?”
“可以,当然可以。”
刘剑平连连点头,转身便带着向南朝书房走去。
朱熙见状,毫不客气地跟了上去。
说实话,他还真没见过别人修复古画呢,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看得到。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还真有些期待呢。
书房很大。
进门正对面,就是一扇硕大的落地窗,此刻,窗帘已经被拉开,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了淡灰色的羊绒地毯上,显得很温暖。
书房正中间,摆着一套海蓝色的布艺沙发,沙发前面,则是一张宽大的茶几。
门的右边,一整面墙壁,全都被原木色的书架给挡住了,上面格子里,则是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
左边的墙壁上,则是挂着几幅书画。
向南只是瞄了一眼,这些书画真迹倒是真迹,不过最古的也只是清末的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看了一圈,没看到项元汴的画,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刘剑平。
“向专家稍等,我把画取来。”
刘剑平一边往书架的方向走去,一边笑道,
“我这人有点附庸风雅,平日里没事就喜欢看看书,看看画,前段时间到香江出差,正好碰上个小拍卖会,就拍了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一幅画,谁知道挂在墙上还没来得及欣赏,就被我那淘气的女儿给撕破了。”
说着说着,他就从书架下方的抽屉里,取出来了一个袋子,然后拿到沙发前的茶几上,小心翼翼地将画取了出来。
刘剑平看了看向南,试探着说道:“这幅画大部分还是完整的,就是下面一点有些碎,我也不懂修复上的事,所以就把所有能找到的碎片都收集起来了。”
“嗯,碎片也是有用的,要是扔掉了,就得补笔,实际上还是跟原画有区别的。”
向南点了点头,对刘剑平的做法表示赞赏。
有些人不懂,看到画碎了,就直接把碎片给扔掉了,如果只是一点点还好一些,如果多了,你让修复师怎么修复?
修复师补笔,那也是根据原作的画意、笔意来的,可不是凭空生造。
站在一边伸长了脖子在看的朱熙,听得一脑袋浆糊,古画碎了也能修复?
还有,那个补笔是什么玩意儿?
说得太深奥了,他几次张了张嘴,看到向南一脸严肃的模样,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咱啥也不懂,咱也不敢问啊。
无知真可悲啊!
刘剑平将古画在茶几上摊开,又将几块比较大的碎片按照原样摆好后,这才说道:
“大概就是这样了,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都在这袋子里了,麻烦向专家看看,这画应该能修复的吧?”
“可以修复。”
向南看都没看,直接就给了刘剑平答案。
只是撕破了而已,这比那些因为保存不善,整幅画作都脆化成碎片的情况好修复得多了。
完全不是问题。
说完之后,他也顾不得去看刘剑平和朱熙的反应,低下头开始认认真真地看起了项元汴的这幅画作来。
这不看还好,一看之下,顿时让他颇有些哭笑不得。
项元汴的画,果然像传说中的那样,亲自题跋,而且就像他盖章一样,根本就不嫌多。
这幅画名叫《精忠柏图》,是一幅立轴。
画面之上,一株枯萎的柏树树干,从左下角斜刺向上。
这柏树尽管已经枯萎了,但树干上伸向各处的树枝,却是笔直有力,给人一种不屈不挠的感觉。
而项元汴的题跋,就题在了画面右侧的中部位置,足足有一百三四十个字之多。
当然,历经数百年,这画面之上的题字,显然不止这一处,清代的书法家王文治也题上了:乾隆丁酉夏六月梦楼王文治观于快雨堂中。
这题字,跟“某年某月某日,王文治到此一游”实际上差不多,反正没什么实际意义。
另一个人,则是王世禛,也叫王士祯,清初的诗人,文学家。
他在画面左边,跟项元汴题跋相对的位置上,“duang!duang!duang!”写了一首诗,不愧是清初杰出的诗人,写了56个字。
三个人的题字,就把这株枯萎的柏树给“包围”了。
除此之外,在画面外的空白处,还有三条长题字,估计这是后来的收藏家给整出来的。
这一眼看去,最吸引人的,不是这画,反倒是这画面上,密密麻麻的题字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因果?”
向南心里忍不住冒出这么一个念头来。
估计项元汴自己也不会想到,他一生都喜欢给自己收藏的书画作品盖章,现在自己的画作上,也被别人题满了字。
真是人生如戏啊!
向南在心里感慨了一番,又朝项元汴的题跋看去:
鄂王祠前指南柏,亦已奇矣,西曹圜(yuán)土间有古柏一株,无枝叶,长二丈有奇,围宽约四尺许,相传鄂王被?(xiàn)同日枯槁,阅今六百余年,坚赤若铁,僵立不仆,号曰:精忠柏。案淛(zhè)省廉访署,南宋时为西曹理刑廨(xiè),鄂王以三字狱含冤殉国,柏亦若恨不能雪王之冤,而含冤以殉王,柏真奇矣哉,余夙聆斯柏之奇,今护瞻仰敬,写是图籍伸钦感云。
崇祯二年三月朔日,檇(zuì)李项元汴写识。
鄂王,是南宋名将岳飞平反昭雪后,所追封的封号。
这幅画,画的实际上是精忠祠前的一棵枯死的柏树,颇有点借物以表意的感觉。
项元汴在画这幅作品时,以以侧锋干笔作皴,和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倪瓒晚年所创的“折带皴”颇为类似,整体画风清润,笔简意远,一股不屈不挠、铮铮铁骨的精气神,跃然纸上。
“果然是个天才啊!”
向南忍不住暗赞了一声,项元汴在书画一道上,自学成才,绘画之上学自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和倪瓒,但更偏爱倪瓒一些。
果然,从这一幅画作之上,已经隐隐有了一些倪瓒的风采。
向南对着这幅破损的画作,看得入了神,站在一旁不知道干什么才好的朱熙终于是耐不住了,但又怕惹恼了向南,只得轻咳一声,低声问道:
“向南,我看你看了那么长时间,这幅画修复起来是不是很有难度?”
向南这会儿也了解得差不多了,此刻听到朱熙的问话,便抬起头来,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问道:
“你想说什么?”
“哦。”
朱熙抬手顺了顺头发,笑道,“要是很麻烦,咱就不修了,费那事干嘛?再买一幅就得了。”
“你就给我闭嘴吧!”
刘剑平一脸无语,狠狠地瞪了朱熙一眼,又陪着笑对向南说道,“他年纪小不懂事,经常乱说话,向专家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年纪小?
我比他更小好不好,还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
这都什么人啊!
向南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他倒是没生气,有钱人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也没必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人家。
人家花自己家的钱,碍着谁了?
“没关系,估计朱熙也是担心我修复起来太麻烦。”
向南朝刘剑平笑了笑,又看了看朱熙,打趣道,“幸好,你没说让项元汴再重新画一幅,要不然,我们都得被你给吓死。”
朱熙:(ノ=Д=)ノ┻━┻
我能不知道项元汴是明代的,我难道看起来就那么蠢吗?!
刘剑平:→_→
是的,你就是这么蠢!
都提醒你别总拿家里有钱说事了,你还说!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文物古董,那才是向专家的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