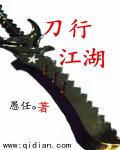独孤影也明白,自己越是生气,狗剩就越是高兴,所以面对狗剩的冷嘲热讽也不动怒,淡淡道:“你别说废话了,想怎么折磨你爷爷,尽管动手就是了!”
狗剩冷笑道:“爷爷,好个爷爷!”
说着重重的在他身上踢了一脚,独孤影早就遍体鳞伤,被他踢了一脚,不觉痛得闷哼了一声。【ㄨ】
只听得狗剩又道:“你倒等不及了啊,好哇!今天就让我这个贱民孙子,好好的伺候伺候你这个爷爷,你的手脚不是还算完整吗?一会儿我就专在你的手脚上做做工夫。”说完就吩咐道:“给他上夹棍、拶指,两刑齐上,看他还嘴硬不硬?”
这夹棍乃是三根杨树木做成,长一尺三寸,同小儿手臂般粗细,两头用牛筋连这一齐,用刑的时候,套在犯人的脚踝,用力拉扯牛筋,三根棍子同时收缩,据说不但能伤筋动骨,在这三根无无情木下活活痛死的人都有。
那拶指也是类似的刑具,用十根手指粗细的竹子做成,专夹人的手指,这些本是朝廷衙门审讯的刑具,也不知狗剩是如何给拿到手里的。
再看两个小师弟,听狗剩的吩咐,忙取过刑具,扯掉独孤影的鞋袜,把夹棍套在他的脚踝上,另外两名弟子也取过拶指,套在他手指上,也不等狗剩吩咐,四人一起用力拉扯牛筋。
所谓十指连心,手指和脚踝上的痛楚迅速传遍全身,独孤影哪里还能够经受得起这般的刑囚,不禁痛得惨叫出声。
“啊……”支持不到片刻,就痛晕了过去。
狗剩让人把他弄醒,然后再次用刑,只到独孤影痛得晕死过去三四次,眼看着不行了,才就此放手,他也怕磨死独孤影,师傅问起没法交代,才让他们撤了刑具。
眼见独孤影双手血肉模糊,脚踝上也是血迹斑斑,乌青一片,趴在地上不停的痛苦呻吟,想到小翠之恨终于报得一点,心中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当即恶狠狠的一脚踩在他手指上,独孤影再次痛得惨叫。
狗剩不禁得意忘形,大笑道:“独孤影啊!独孤影,你可别怨我,要怨,就怨你是独孤家的人,如果不是你们独孤家的人向我们透露消息,我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跟雄霸西域近千年的独孤世家叫板嘛?”
“你……你说什么?”独孤影闻言大惊,当下也顾不得疼痛,挣扎着问道。
狗剩看着独孤影的表现,心道:师父说的没错,这样果然有用,他继续道:“好!我今天就做做好事,让你死也死个明白,具体经过我并不清楚,但是,千真万确,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有独孤家的人跟我们合作,为什么合作,是那个人想成为独孤家家主,而不是所谓的外院长老。”
独孤影听了狗剩的话,愣住了,作为千年世家里面的弟子,他自然知道嫡传和外院之间的区别,说白了就是主次之分,嫡传可以拥有外院近乎五倍的资源,他也晓得,一直以来,独孤家就有嫡传和外院之争,但没有想到,外院为了彻底的打垮嫡传,不惜出卖独孤家的利益。
“不会的,不会的,你骗我,我不相信!”他声嘶力竭的叫道,虽口中叫着不相信,心中却痛得难受,仿佛被谁狠狠的刺了一刀,眼泪也随着流了下来,他这一大叫,不免牵动了伤势,忍不住剧烈的咳嗽起来。
狗剩见他流下泪来,倒不觉呆住了,本能的松开了踩住他的手,想自己这半天时日来,无论如何用酷刑折磨他,他都处之泰然,从未见过他伤感流泪,没料到短短几句话,竟然可以让他如此伤心痛苦,不知不觉中,他对于独孤家的那份痛恨莫名的减轻了不少。
眼见他剧烈的咳嗽,不停的咳出血来,而血肉模糊的双手,隐隐之间已见白骨,也不停的流下血来,散发赤足,偏体鳞伤,却依然掩不住那公子气息。
狗剩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轻快的咳嗽声,知道是了然找他,忙推门而出,然后紧走几步,来到了然跟前道:“师父,该说的弟子都说了,不该说的弟子也想法设想的编了些瞎话跟他说了”。
“他有什么反应吗”了然突然问道。
“刚开始一句话不说,弟子说有独孤家的人做内应,他大呼不相信,还流了许多的眼泪,弟子猜测,可能是刚才给的消息对他打击很大,不然不会这么难过”狗剩将独孤影的表现一五一十的对着了然说了一遍,不知为何,他觉得自己这个师傅对于独孤影有着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具体什么感觉他也说不上来。
了然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方还带着血迹的白色手帕,血迹因为年长的缘故,都有些发黑,在手帕的拐角处,绣有一朵红色火焰标志。
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爱人般,好一阵才将它递给狗剩,道:“你一会进去,将这个东西装作无意掉下的样子让他看到,最好能留在他的手里”。
狗剩接过手帕道:“弟子明白,只是师父,弟子不解,独孤影仅是外院管事的儿子,又不是嫡传,我们如此算计有用吗”?
了然看了狗剩一眼道:“独孤家就像一块巨石,我们搬不动,也扛不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它打碎,一车车的拉走,要想打碎巨石,我们必须的找到巨石的缝隙,然后根据缝隙的大小,一步步的深入。独孤家的内外院之争,就是他们的裂缝,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裂缝中打上属于我们的楔子”。
“弟子明白”狗剩说完,回到了关押独孤影的小牢房,看着远去的狗剩,了然喃喃道:“大哥,父亲,你们的仇我一定会报”。
再说狗剩,他回到牢房,也不知怎么才能完成了然的嘱托,将那个手帕神不知鬼不觉的掉在他的面前。
思前想后,他决定牺牲自己,当即蹲下身子,抓住独孤影的一只手,问道:“痛得厉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