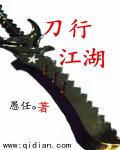葛南诗脸上的神情缓和了一些,略一沉吟点头道:“你做的对,为师相信你所说的话,但你可知道此事已闹的沸沸扬扬,过几天西域少林的雾灯大师便要带着了然前来对质,你师伯更是请了江湖数十位宿老人物前来见证,一旦实情为外人所知,那我们华山派今后还有何颜面在江湖上立足?这后果着实不堪设想,雪儿,师父的话不知道你听没听明白?”
梅落雪望着满面肃容的师父道:“可是,师父,了然师兄他救了徒儿一命,他……”
葛南诗叹了口气,打断梅落雪的话道:“雪儿,徐师侄触犯门规,妄图侵犯于你的事,今后不要再和任何人说起了,师父定然会要他还你一个公道,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怎么把几天后的事情应付过去?”
梅落雪道:“师父,了然师兄为人光明磊落,他不会藉此机会故意来损害华山派声誉的,或许他只想洗清冤屈罢了。”
葛南诗盯着梅落雪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傻孩子,你虽天赋过人,可终究不识人间险恶,近年来我华山派在你师伯的经营下欣欣向荣,声威直追少林与南宫世家,大有撼动前二者正道牛耳之势。就算了然没想借题发挥,那雾灯大师和他的几个师兄弟却未必肯如此轻易的放过我们,要是把这事情抖出去,我们华山派的清名,还有数百年来辛苦建立的基业势必受损,短时间内怕再也无力与少林抗衡,这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法子,他们何乐而不为?”
梅落雪一怔,在她看来原本十分简单的问题,师父却看得如此复杂,甚至牵涉到了门派之争。
她犹疑道:“师父,我们和华山派素来同列江湖正道七大门派之中,同气连枝,渊源深厚,雾灯大师据说亦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应该不会做出这等事情吧?”
葛南诗挥了挥手道:“同气连枝不过是表面罢了,试问各大派谁不想执江湖牛耳、光大门户、领袖群伦?莫说雾灯大师,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心底怕也有这念头,只是不说而已。你还是太天真了些,不懂得那些勾心斗角的龌龊伎俩。”
虽然听师父这么说,但梅落雪想到这些日子与了然相处的感受,直觉他们该当不会如师父所说的那般阴险卑鄙。
可从小对她而言,葛南诗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她更把师父当成神仙一般来看待。
因此尽管心中迟疑,她还是想着:“也许是师父从没见过了然师兄,所以才会这么想吧。”
葛南诗凝视这个从小在身边长大的徒弟,梅落雪虽沉默不语,但显然对她的话已不再是深信不疑,心中转了数个念头,忽然语气郑重的问道:“雪儿,你拜在为师门下已有十年,这些年为师待你如何?”
梅落雪听师父问得奇怪,但还是低头轻声答道:“师父虽然对弟子十分严厉,可雪儿明白那是师父一片苦心要造就弟子。在雪儿的心目里,师父待雪儿就如同娘亲一般。”
葛南诗紧绷的脸露出一缕笑容,点头道:“难得你这么懂事,为师没白心疼你一场。雪儿,倘若是师父有事要求你,那么你也会答应,对不对?”
梅落雪一震,赶紧跪倒在葛南诗面前,低头道:“师父,您这么说折煞雪儿了,无论师父要雪儿做什么,雪儿岂有不遵命之理。”
葛南诗的笑容更加温和,伸手将梅落雪扶起道:“好孩子,为师果然没看错你,师父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为了我们华山派的未来,不管那日的真相如何,你都要咬住是了然企图对你不轨,万万不可说出你徐师兄来。”
梅落雪“啊”了声,抬头望向葛南诗,迎面撞上一双锐利如锋的眼神。
她万没想到师父居然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芳心中乱成一团,迟疑的说道:“可是师父,这么一来,雪儿岂不是恩将仇报,要陷了然师兄于不义了么?”
葛南诗面如寒霜,低声道:“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我也晓得这么做委屈了了然,可我华山数百年基业,实不能因此毁于一旦!要是那日侵犯你的是钱宋两个师侄也就罢了,徐文峰可是你掌门师伯的唯一心血,更是我华山派未来百年的期望所在,若此事传扬出去,不仅徐文峰声名扫地,你掌门师伯的面子也不好看。万一让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在背地里扇风点火,说什么堂堂正派名门的掌门弟子做此令人不齿行径,我华山派上下数百同门的脸面又往哪里搁?更不用再奢谈什么争雄江湖,领袖正道群伦了。”
她伸手轻抚梅落雪如云的秀发,目中露出慈爱光采,喟叹道:“雪儿,为师已经六十多岁了,这些日子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天命将尽,中兴松溪苑一系的重任,迟早也要落到你的头上,为师平生最大憾事,便是未能为师门光大尽到心力,这遗憾也惟有你来为我弥补了,这番苦心,希望你能懂得。”
梅落雪心乱如麻,对师父要将衣钵传承于她的承诺更没半点欣喜,只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做这般陷害了然的事情。
她下意识的连连摇头,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才好。
葛南诗见爱徒迟疑不语,面色渐渐沉下道:“怎么,雪儿,为师这样苦口婆心的恳求你,你却还不肯答应么?”
梅落雪仿佛是坠入汪洋中的一块浮木,觉得自己随波载沉载浮想抓着什么,偏又什么也构不到。
十余年来,师父在她心目中,恍若正义与公道的化身,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如谕旨纶音,如今,要她颠倒黑白去冤枉了然,却犹如一柄大椎,无情的砸碎了师父在她心中树立多年的神像。
她鼓起勇气挣扎道:“师父,雪儿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陷害了然师兄?您一直教导弟子秉持正义,匡扶天道,难道这都是在欺骗弟子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