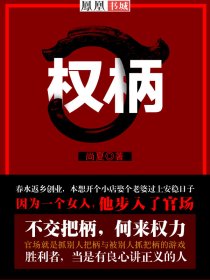第一批进来的,正是白天抬她的几个壮汉。他们做这种事也不是头一回。医院里女病人不少,他们把她们当作乐子,烦闷时,无聊时,饥渴时,她们就成了动物园里关着的动物。有几次晚上,他们趁黑摸进病房,对着年轻的病人做着猥亵的动作。他的耳朵里听着这些不堪入目的声音,怒火中烧,都快控制不了自己,想翻身而起,制止他们罪恶的行为。但理智告诉他,这样做无济于事,根本不能制止他们,他自己也会暴露,得到的会是一顿暴揍。他经常对那些被精神病的人说,那药丸不能吃,并把他的方法告诉他们。
这几个壮汉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病房。他们虽只是打杂的,在这些神智不清的精神病人面前,却有着滔滔不绝的优越感,动不动就说这些神经病。他们也知道,病人晚上睡前会吃一种特殊的药,吃了以后就如中了定身法一般,身体是僵的,意识是迷的。所以,他们进到病房,根本不用害怕,如入无人之境。他们要提防的,就是医生与护士,这些人有时会训斥他们,说他们没文化没素质。这样骂,他们一点也不生气。没文化总比神经病强。
新来的女人太有吸引力,虽然医生已经告诫过他们,他们还是来了。摸一摸也是好的,他们抱着这样的目的。
女人的病床在第三排第四个,他们记得很清楚。他们对这里的每一张床的位置上面的病人都很熟悉。
原本,这些床就是他们摆的。
病房里的灯已经灭了,但走廊里的灯光透了进来,里面并不昏暗。病人们一个个蒙着头,雪白的床单罩住了他们的全身。换了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进到停尸间。
他们很快到了第三排第四张病床前,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手心开始冒汗。这女人太漂亮了,平日里哪有机会接触这等有气质有文化艳丽无比的女人。现在她就在身边,毫无动静,可以任他们胡为。想摸哪里摸哪里,一想到这点,个个乐开了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像过大年似的。
他们分立两侧,不约而同地把手伸进了被窝,目标是胸部与大腿。他们中两个是结了婚的,两个谈过女朋友,对女人不算陌生。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们期待着不一样的触觉,非同一般的体验。
可他们面面相觑。这种感觉特别是特别,但不美好,甚至,还不如他们过往的经验。
这是怎么了?难道有些女人只是看上去很美,摸上去不美?不会呀,他们白天还抬过她呢,那种触觉到现在还回味无穷。就奔这种感觉,他们睡不着,惦记着。这不,他们来了。
摸着的两人蓦然觉得,这不是一个女人。这胸太平了,太实了,女人没有这样的。真是活见鬼了,难道这女人会变身?白天是个美女,黑夜是个丑男?
摸着大腿的发现这腿坚实有力,如牛腿马腿,女人的大腿长在这样,谁还敢上?他们继续往上摸,这才知道,这原本就是个男人。
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抽出手,再次面面相觑。
其中一个想掀开被子,看看刚才摸的到底是谁。太诡异了,这么变成男人了?
可这人的盖在脸上的被子捂得严严的,怎么拉都扯不开。正东拉西扯之际,又有人进来了。
他们立刻蹲了下去,做狗爬状,从另一侧快速地离去了。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主治医生。他也惦记她,想来看个究竟。服了药后的她,沉沉睡去,睡姿同样优美吧。
他来到第三排第四张病床前,站在一侧,仔细地看看床上之人的睡姿。奇怪,并没有他想像中那种S形,而是直挺挺的,从上到下,没有起伏。这是她吗?他怀疑着,想掀开被子,一看究竟。
可他一伸手,发现被子如同磁铁一样地吸在此人的脸上,怎么也弄不开。他更想看个究竟了,双手一起上,像鲁智深拔树那样,用着身上的所有力气。
床上的人却突然松开了,原本重若千斤的被子一下变得轻如鸿毛。
他提防不及,整个人就向后倒了下去,重重地撞在地上。他清楚地听到尾椎骨与地面撞击发出的“咔嚓”声。
骨折了。
他痛苦地叫了一声,却无人喝彩。这里的人还是像死去的一般,毫无动静。
想站起来,试了试,痛得厉害,骨头疼,屁股痛,这下摔得不轻。他想叫人来扶一扶,环顾四周,才知道没有可以使唤的人。
他强忍疼痛,扶着床柱,站了起来。他还是想看清楚床上之人是谁。
果然不是她,而是个男人。他双目紧闭,纹丝不动,已是“熟睡”的模样。
这个病人他认识,年轻小伙,来了一段时间了。他怎么睡到这床上来了?她呢?睡哪了?难道他们换了床位?
他想摇醒他。试了几下,刚才摔的地方疼得厉害,稍一用劲,就支持不住。而且,他知道,服了药的病人,怎么摇都不用醒的。
他只能苦笑,怎么能与神经病计较呢?
只能撤了。他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病房,心里想着,要赶快去做个检查,看看是不是骨折了。真是如此的话,问题大了,伤筋动骨一百天,想对这个漂亮女人做些什么都不行了。
做B超做透视的人早已下班。他只能忍着,等明天的到来。
晚上,他睡不着,这一跤摔得太冤了,这应当算公伤吧,对,得找人证明一下。他披衣出来,把摔伤的事讲给几个当班的护士听。她们非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哈哈大笑,笑得前俯后仰,完全失去了女人的矜持。在这里,时间久了,人人都变得神经质了。他悻悻地走了。
他隐隐约约地觉得,那个男孩子是故意为之。果真如此的话,这人丢大了,在精神病院,医生被一个称为神经病的病人所戏弄,说出去,一世英名毁矣。他越想越气,恨不得立刻返回病房,找那个男孩子问个究竟,查个明白。
可屁股越来越痛,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了。
他搽了些药。精神病院并没有骨科,如果严重的话,还得去别的医院看看。
第二天一早,痛了一夜的他急匆匆地作检查去了。夜里,他几次三番想起来看急诊,想想还是算了。
章依娜醒来的时候已是上午九点了。怎么睡得这么死,睡到九点?她拍了拍像要裂开一样的脑袋,虽然睡得时间很长,但头是晕的。她奇怪的是,怎么睡到这张床上来了?她记得昨天是睡在那张床上的,相隔有十几米呢。难道记错了?她努力想回忆以前的事情,却非常地困难。只有一动脑子,头就发痛。
昨天见到的阳光病友走了过来,坐在床前。他的笑容依旧灿烂。
“睡得如何?”他问。
“还行吧。你呢?”她要让自己显得精神一些,也笑了笑。在这里,笑容是十分稀少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痛苦与沉重。
“以后睡前千万不要吃所发的药了。”他靠近她的耳边,轻声对她说。
“药有问题?”
“是的。对身体危害很大。”
“能不吃吗?”
“尽量不吃。”
“你没吃?”
他点了点头,并三言两语向她说起了昨晚的事。
她听了目瞪口呆。要不是他进行了床位的调换,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她充满感激地看着他。
“多亏你了。”
“别这样说。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早点出去。不然,迟早会被他们逼疯的。”
*****************************
天无绝人之路。
还记得雨燕吗?春水回到了艾城,她也辞去了城管局的工作,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勤奋好学的她,成为了市检察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三年过去了,她已能独当一面,解决了许多棘手的案子,深得领导的赏识。但能力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像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样。有些案子,因为权力的干扰,不了了之。她并没有因此丧失热情,继续全力以赴地履行着一位检察官的职责。她是个肯学肯动脑子的姑娘,又有正义感,这样的检察官真是少之又少,所以上上下下都很喜欢她。她没有心机,但不单纯,做事很有分寸。
她这次到精神病院来,就是调查一个官员的贪腐案。说是官员,其实是财政局的一名普通科员,没什么级别。可就是这样看上去没什么权力的人,却一口气侵吞了五十万。对这种没级别的人的调查,自然落到了她这种同样没什么级别的检察官身上。这人伸手拿钱时胆子很大,事发后胆就吓破了,一见到调查人员,就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甚至尿失禁,很快发展成精神病,被送到了这里。很多人说,她这是装疯卖傻逃避惩罚的,所以,雨燕到精神病院来,想搞清楚她是真病还是假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