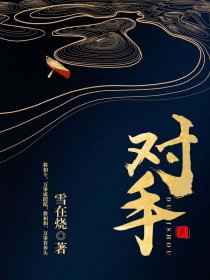项白看他一眼:“你倒是大方,你老板知道吗?”
“嗐,知道也不能怪我,您是常客,就凭您买的那些酒还不值这几个茴香豆吗?”
项白努努嘴说道:“也是。”
小卢打量他两眼,说道:“怎么着,心情不好?”
“说不上好。”项白说道。
“我猜是因为……女人?”
项白瞧他一眼未置可否,端起酒杯尝了一口,辣的嗓子眼儿疼,他皱皱眉头咽下去,不一会儿便满口醇厚的酒香,这才说道:“算是吧。”
“是为了畅春楼的迎春?”小卢试探道。
“嗯?”
“那要不然,是为了怡红院的胭脂?”
“这都是谁啊?”项白颇有些哭笑不得。
“都不是?”
“不是。”项白说道。
“也对,那种庸脂俗粉,没什么意思。”
“庸脂俗粉?”项白笑了笑说道,“没看出来你还挺有品位?”
“那是,我没品位,您有不是?”小卢说道,“都不是,那就是追月楼的照雪姑娘。”
“更不是,什么照雪姑娘,听都没听过。”
“哎呀,所以说您才心情不好嘛!”小卢神秘地笑道,“我这里有个东西,您要是瞧见了,那心情自然就好了。”
项白看着他,只觉得小卢的笑十分猥琐,却还是有点好奇忍不住问:“什么东西这么神?”
小卢从腰带里摸出一块丝帕,帕角绣着照雪二字,只是那两个字不是用寻常丝线秀的而是人的头发。
“这是什么意思?”项白问。
“呦,您都不知道我哪儿知道。”小卢又笑道,“要不,您自个儿去追月楼问问去?”
项白咧嘴一笑,把帕子收起来:“看心情吧。”
“那是,去不去都得您说了算不是?”正乐着,小卢眼皮儿一抬立刻又换了一副无可挑剔地热络面孔,说道,“这是什么风,把咱们洪四爷也刮来了?”
“能是什么风,西北风!这天儿真是冷,太他妈冷了,装满。”洪鹰把酒囊递给小卢粗声粗气地说道,“这不是项公子吗?”
“洪四爷好。”项白原本酒量一般,又没吃什么东西,这会儿已经有点儿上头了,只虚抱了个拳也没起身。
“项公子,怎么独自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洪鹰顺便坐在项白对面,“莫不是案子查的不顺利?”
“顺利不顺利,洪四爷不知道吗?”项白说道,“就凭您故意隐藏行踪,这案子能顺了吗?”
“这个,我也算不上故意隐瞒。”洪鹰笑道。
项白撑着头,他确实有点儿上头,笑道:“那照您看,得怎么着才算?”
“这事儿我已经跟魏捕头交待过了。”洪鹰说道,“昨天晚上我的确是送下三哥打算回自己房里,可是我路过二哥院子的时候看见一个黑影,这才好奇追上去。”
“你也看见一个黑影?”
“怎么,还有别人看见了?”
项白没有回答问道:“然后呢?你追上了?”
“当然追上了,我还和那人过了两招,我就是那个时候手腕才受了伤。”
“在哪里?”项白抬起头,眯着眼睛,似乎在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就在聚财厅后面的空地上,他当时似乎在烧什么东西,因为我闻到烧焦东西的味道。”洪鹰说道,“我刚打算靠近点儿看看就被他发现了。”
“然后呢?”
“然后就跟他动手了。”
“唔,什么时间?”
“从我送下三哥到跟他动手,前后最多一刻钟。”
“唔,一刻钟。”项白撑着头想了很久才说,“丑时一刻。”
洪鹰想了一会儿点点头:“差不多吧。”
“不……丑时二刻。”项白晃晃头。
洪鹰又想了想说:“不是一刻就是二刻。”
项白紧皱着眉头,好像很难受似的。
“我后来想了想,那正好就是二哥被害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人就是凶手。”
“嗯,我也是这么想。”项白眼神木讷,敷衍似的说道,忽然又瞪起眼质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项公子,今儿早上可是你们说的,凶手很可能就在我们几个里面,我又刚好在那个时候遇到那个人,换成你是我,你会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儿把这事儿说出来吗?”
“哦。”不过转瞬之间,项白又醉眼迷蒙了,嘟囔道,“你怀疑你遇到的人就是凶手。”
洪鹰点点头,有点儿苦恼似的:“我不是说了吗,我怀疑那是凶手。”可是项白双手捧着头像是睡着了,他碰碰项白的胳膊肘,“项公子?”
“嗯。”项白猛地抬起头,“我没睡。”
“哦。”洪鹰又说道,“他穿着夜行衣还蒙了面,所以我认不出他的样子。”洪鹰又想了想说道,“不过,我跟他交手时觉得他的身形很眼熟,有点儿像……老五。”
“唔。”
洪鹰说道:“其实大哥说的有道理,能杀得了二哥的也就我们几个,三哥醉的厉害,大哥就更别提了,别说让他杀人,杀只鸡也做不到,说到底,最有可能的也就是我和老五,既然不是我,那就是他。”
“嗯。”
“我知道,我说了你也未必信,说不定更怀疑我。”
“嗯。”
“可是若我是凶手,又何必多此一举,越描越黑呢?”
“……”
“项公子?项公子?”洪鹰又碰碰他的胳膊肘。
“呼……呼……”
洪鹰叹口气,有点儿不悦似的嘟囔道:“这到底是听见了还是没听见,我不会是白费口水吧……小卢!”
“哎哎!来了!”小卢早瞅着事情不对,怕自己一个不留神听到不该听到被灭了口,早就溜到一边儿去了。
“装好了没有?”洪鹰问道,他嗓门儿大,项白叹息一声换了个更舒坦的姿势趴着。
“好了好了,您的酒。”
洪鹰看看项白,扔下几个铜钱道:“行,老子还得值夜呢,走了。”
“哎,四爷儿慢走。”
小卢见洪鹰走远了这才过来叫项白:“项爷儿,您醒醒呐!”又自言自语似的说,“哎呦,我的爷儿,可真没见过您这么心大的主儿,您是真不怕让人给咔嚓了呀!”
“你哪只眼看出来我不怕?”项白醉醺醺的说道,然后悄悄露出一只眼睛,“走了,可走了。”他坐直身子伸个懒腰,然后掏出几个铜板放在桌子上,“我也走了,可冻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