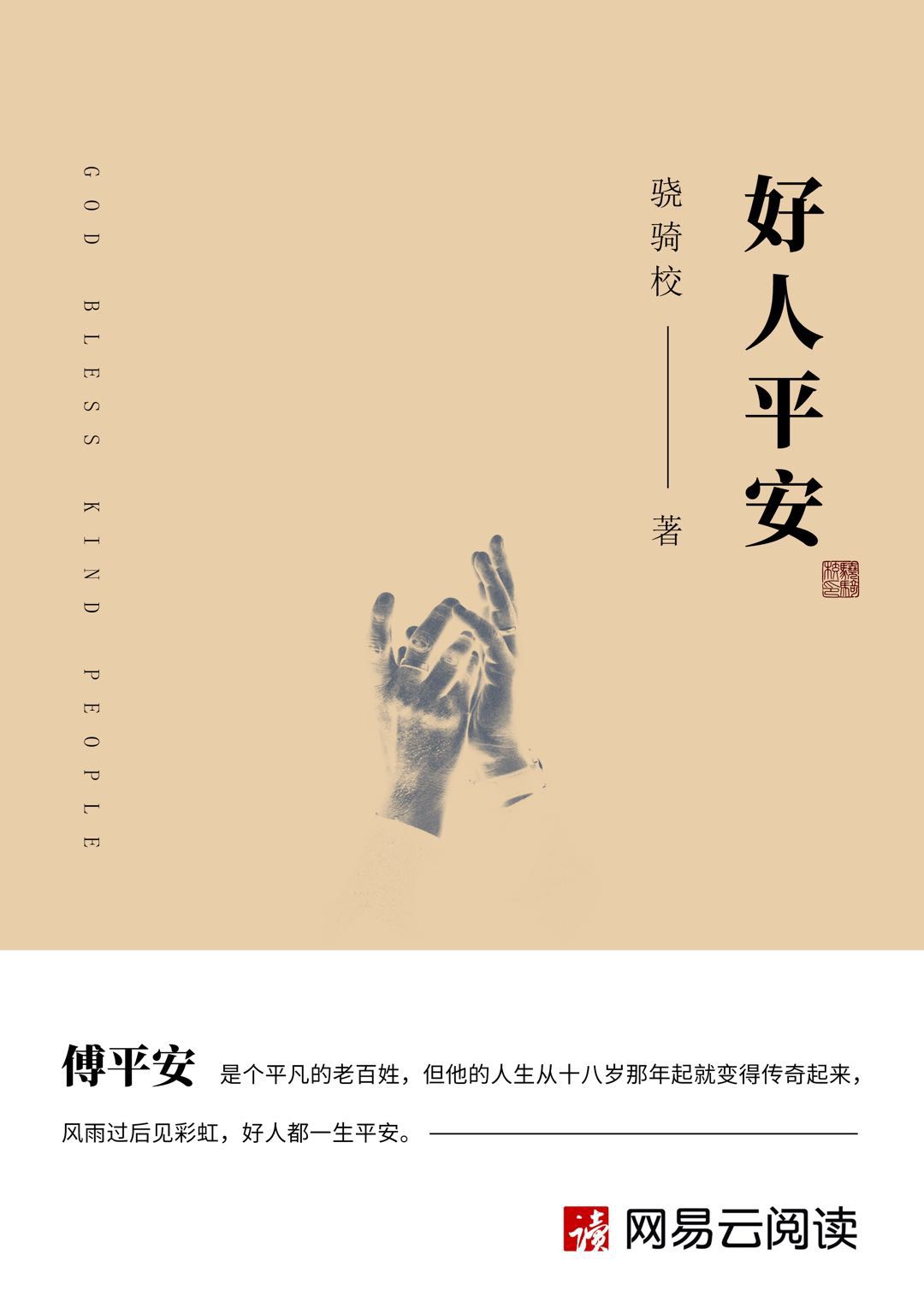63
在一个月前,南绝对想象不到自己有面色自如踩过动物粪便的勇气。现在,他根本不在乎脚下那软趴趴黏糊糊的是什么玩意儿,让他感觉难受的只有空气中那种隐隐约约的酸臭气――
“这也叫清理过?”东恼火地埋怨,“床单翻过来就能接待客人?这能□□铺吗?这是猪窝吧!”
南用两根手指把木床上那条看不出颜色的布料揭起来,冲东打个眼色,“开窗户,东,这里的空气都快烂掉了。除了家具,其他东西都丢出去。”
格洛丽亚很有先见之明,那两个年轻农民“打扫”过的屋子果然无法住人。向阳面的两间客房,一间比一间更脏、臭、混乱,自告奋勇来打扫的托莱兄弟算是大开眼界。
“找他们借扫帚,地上都是鸡粪啊!”
“那条凳子也搬走,脏得太离谱了。”
“这袋子……里面是发芽的土豆?!这玩意儿怎么丢在这里!”
两间客房清理出来的杂物、垃圾、散发着奇怪臭味的可疑物体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忙完这些的托莱兄弟累倒是没觉得累,就是嗅觉差不多麻木了。
格洛丽亚走进客房看了看,不算太宽的屋子里只剩下床、桌椅、还有靠墙的柜子,床上的东西全都丢了出去,换上了飓风女士自带的铺盖,看起来倒是勉强能入眼了。
“还不错,嗯,小伙子们挺能干。”格洛丽亚拍拍东的胳膊、南的肩膀,“瞧你们脏的,去换洗一下吧,我让萨姆尔准备好热水了。弄干净了赶紧吃晚餐,早点儿休息明早好出发。”
托莱兄弟转身往外走,南对兄长说了句,“东,你先去拿水,我去把陆行鸟背上的行礼架撤下来。”
“哦,对了。”格洛丽亚想起了什么,“只有两间客房,得委屈你们挤一挤了啊。”
“好的。”托莱兄弟习惯性地回应了一句,走出去几步才想明白格洛丽亚话里的意思,脚下一滑。
……跟跟跟跟安格斯挤一间?!
安格斯没理会颐指气使的格洛丽亚、也无视了忙忙碌碌的托莱兄弟,他将双手拢在袖子里,以年长者特有的缓慢、沉稳脚步在庭院里漫步。这座农家小院算是规模比较不错的那一类,整齐的砖石累就的屋子、半人多高的院墙,除了用于居住的主建筑、宽敞的马厩,后院还有三间并排的库房。
普通农夫家的库房大多用来堆积麦秆、木材、杂粮、农具,多数只是在木架子上铺一层干草了事;萨姆尔村长家的库房倒是颇具规模,和主屋一样的石料建筑,紧闭的木门上挂着铁锁。
对于普通人来说铁器是珍贵的,用得起铁锹、铁犁头的都算是自由民中的富农。三间库房木门上的粗大铁锁目测也有好几斤重,不由得安格斯不留意。
“这位……老爷,您在看什么呢?”萨姆尔不知何时出现了,笑容可掬地躬着身,隐隐挡在安格斯前面。
安格斯停住脚步,兜帽阴影下的目光扫过萨姆尔看似忠厚的苍老面孔,不发一言。
萨姆尔有点儿犯嘀咕,精明如他也完全看不出这个斗篷怪人的深浅,态度上表现得更恭敬了,“老爷,我们准备好热水了,给您提到房间去里吗?”
安格斯慢慢转过身,慢慢往主屋方向走去。
萨姆尔在他转过身去后脸色就沉了下来,盯着安格斯的背影,看似浑浊的双眼中精光闪现。
“装神弄鬼的家伙……”这位村长眯起眼睛嘀咕了一句,脑中浮现格洛丽亚那身金光灿灿的打扮、陆行鸟屁股上那高耸的行李架,藏在衣袖里的手松开了又捏紧。
南费力地把行李架抗进房间时东也把大木桶拖进来了,往里面哗啦啦倒水时安格斯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
东一哆嗦,稍微洒了点儿水到自己手上,烫得他差点儿跳起来。
安格斯没去废话三个人是不是要挤一个房间的问题,也漠视了僵硬起来的托莱兄弟,他反手关上门,没见他做了什么动作,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的斗篷忽然分解成一团黑雾,并很快消散;自然地看向东,微微一颔首,“不要太烫。”
“好的。”东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而后伸手试试水温、觉得差不多了后恭敬退后半步,半点儿也没有抗争一下“这是我给自己准备的洗澡水”之类的意识。
安格斯伸手去解立领长袍上衣的扣子,看向正整理行李架的南,“拿出那套黑色常服。”
“诶?哦。”一起旅行这么久,这还真是安格斯第一次正面对自己说话,南有点儿受宠若惊。不过他这种小激动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安格斯当着他们兄弟俩,旁若无人地脱起衣服来了……
略有些宽松的立领长袍下是棉布里衣,褪下里衣后,暴露出柔软布料下雪白细腻宛若无暇美玉的肌肤,他的身体并不像外表看去那样弱不禁风,反倒是拥有着均匀结实的肌肉、完美有力的曲线;随着他的动作,丝绸般的黑色长发流水般倾泻而下、直垂到光|裸的腰际……
“……”南默默垂下头整理行李,东眼神儿发直了几秒后,也凑到他身边去帮忙。
明知道这个家伙是个多么危险的瘟疫之源,还会觉得对方“美丽到让人心颤”、“产生咏唱赞美诗的冲动”什么的,真是太糟糕了。
这房间不算太窄,但淅沥水声萦绕耳边,再加上不时浮游到鼻息间的水汽;明明同处一室洗澡的是个男人,托莱兄弟却是慢慢地感觉面部火烫起来,根本就不敢把目光往那边移动。
……太糟糕了。
东苦着脸对弟弟做了个口型。
……忍耐。
南只能如此回应。
煎熬持续了十多分钟,期间,南硬着头皮把从安格斯的箱子里找出来的常服送到了浴桶旁的椅子上。
得庆幸男人洗澡总是要比女士快得多,安格斯从浴桶里走出来用东准备的毛巾擦掉水汽,慢吞吞换上南准备好的常服,脚下浮起一道黑雾,笼罩全身后化为包裹住全身的斗篷,又回复了斗篷怪人造型。
大约是感谢托莱兄弟的“服侍”,安格斯再次冲兄弟一颔首,打开门自个儿走了出去。
托莱兄弟长出口气,揉着蹲麻的小腿站起来。
南神色复杂,“看来末日审判接受我们作为同行者的身份了……”
东挤眉弄眼,“我刚才偷偷看了下,他有‘那个’。”
“哪个?”南一愣。
东点了点男人都懂的重要部位。
南点儿被口水呛到,“你都在注意什么呢!”
东嘴里发苦,“你看……凯丽那种都还是女人呢……我估摸着没准儿这又是一个凯丽呢?你看那张脸……”
南气过头反而发不出火来了,用力揉眉心,“你就有点儿紧张感吧……怕他怕得要死的不就是你吗?”
“总想着沉重的东西,人都得发疯。”东说道,完了他沉默了一下,神色郑重地问,“现在有个事儿倒是很紧迫……晚上怎么睡?床可只有一张。”
“……”南沉默了。
阔别多日的、正式的晚餐,虽然汤里有些不明物漂浮、虽然面包又黑又硬、虽然……好吧,麦片还是挺可口的,应该是新麦;土豆饼的味道也不错,沾了辣酱以后让多日没吃到甜味以外香料的托莱兄弟感动万分。
萨姆尔家的房间不多,把餐厅让给了客人们后,他们一家子只能窝在厨房里吃。南观察了一下他们的食物,看到那清淡的汤和更黑更硬的面包、而且还没有麦片和土豆饼,忏悔了一下自己的不知足,默默地与从未吃过的粗麦黑面包奋战。
“……你蠢吗!不能吃就别吃啊!”半小时后,托莱兄弟与安格斯的房间里,格洛丽亚跳脚,南捂着肚子脸色苍白地蜷在椅子里。
“你们那个‘白光一闪’治不了食物中毒?”格洛丽亚气呼呼地问东。
“女士……圣光祝福可以治愈普通外伤、可以驱散低阶诅咒、可以加快内伤的恢复速度、可以――”
“就是不能解毒是吧。”格洛丽亚打断他,恨铁不成钢地看向南,“你也跟东学学变通啊,又不是讲究餐桌礼仪的时候,谁还逼你在这种地方一定要吃完餐盘里的东西了?”
“……浪费食物不太好……”南虚弱地说。
“你蠢吗!哪还有浪费的?刚才萨姆尔家只有那父子三人分到吃的,他妻子和女儿眼巴巴地往咱们这边看了半天你没瞧见?”格洛丽亚又跳脚了。
“……”南瞠目结舌,“这、这太不卫生了吧?”
格洛丽亚哭笑不得,“大少爷!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兄弟似的还挑肥拣瘦呢,有得吃就不错了。”
南无言以对。
“算了,你好好休息――啧,鬼知道还会有你这种吃个黑面包就食物中毒的娇气包呢?我带的解毒剂可没这功效。”飓风女士也只能服气了,“看看到明早你能不能好一点……东,明天你跟我去附近的集市看看,有草药、药剂之类的东西的话就弄点儿防身。”
“好的。”东连忙点头。
格洛丽亚看向老神在在坐在另一边的安格斯,“明天你留下来看着点他,这地方……单留个病号不安全。”
专注于手中黑皮书的安格斯抬头看过来,垂了下眼皮算是应答。
“你们三个挤一间是不方便了点,不过咱们最多也就呆一两天,忍耐一下吧。”
格洛丽亚丢下这么一句就回房了,东拿毛巾擦了下南额头上的汗,偷瞄下碳盆前稳如泰山的安格斯,再瞄一眼唯一的一张床,犯难了――他这位兄长还是很合格的,自己并不介意打地铺,但还是希望不舒服的弟弟能好好躺一下。
安格斯似乎是明白了他的心思,视线离开书本投了过来,简短地吩咐,“扶他去睡。”
“好的。”东心中一喜,手上用力把南抱起。
南是想要拒绝的……首先,身为骑士抢施法者的床,他觉得自尊上过不去;其次,不管安格斯是不是显露出细小的“善意”,他都没打算放弃对对方的“监视”;不过他大概是高估了自己的抵抗力,在身体被哥哥抱起的一瞬间一股倦意冲上头顶,眼睛一闭,都还没挨到床就沉睡过去了。
之前数天的疲惫爆发出来,南倒是睡得挺安稳的。东就纠结了,把准备好的木板放到地上时犹豫着两个地铺要怎么打,挨近了似乎不太礼貌,隔远了又好像他对人家多防备似的……安格斯这次没理会他,看了会书后合上书本,保持着坐姿、头微微一垂,眼睛就闭上了;东偷偷摸摸打量了他半天,直到确认他确实是坐着就睡着了才敢轻手轻脚地铺棉被……
明月高升,万籁俱寂;咋一看去,广袤平原上静静矗立的小村静怡朦脓。
萨姆尔家的小院里,主屋内,主人家卧室木门被轻轻地推开。
佝偻的身影慢慢地从门内走出,手中提着一根拐杖,却没有用来触地,而是小心地虚提着、垫着脚尖、慢慢挪到餐厅中央,鬼鬼祟祟地望向客房的方向。
静静地站立了一阵,确认那两扇并排的木门没有任何异样后,这个佝偻的身影扭转方向,悄悄地出了正门。
院子里的黄土地面能够吸收脚步声,萨姆尔踩到泥地上后,弯曲的身体瞬间绷直,脚步也敏捷起来。靠近相邻的客房窗户时,他又再度恢复佝偻模样,杵着拐杖,故意走出不轻不重的脚步声。
绕着自家的院子转了一圈,经过马厩时,他进去看了一眼照顾骡子和客人陆行鸟的儿子有没有偷懒,见小儿子兢兢业业地守着,萨姆尔装模作样地训导了他几句,又返回客厅,进入自家卧室。
应该是男女主人居住的主卧室里,他的妻子却不见踪影,大儿子反倒是一脸急切地等在里面。
“怎么样?父亲,能动手吗?”与萨姆尔一起出过村的年轻农夫压低了声音问道,手中把玩着一把看上去有些年月的斧头。
“稳重些,麦克,你这样子能做成什么事?”萨姆尔挺直腰背,鼓着眼睛呵斥了一声,走到桌边坐下,自己给自己倒了半杯酒。
“父亲,那个女人鞋子上的宝石就值不少钱了――”麦克显然是无法像父亲那样沉得住气的,“你不是说那女人绝不会是行者吗?”
“当然不是,行者的走路方式不会是那种样子、也不会睡得那么死。你父亲我虽然没有通过职业考核,至少也做过见习行者。”萨姆尔冷哼一声,“但是她那枚金牌猎人的徽章是真的,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弄来的……但我们也必须小心。”
“管她怎么弄来的呢?晚餐的时候我留意过了,他们那一行人都把土豆饼吃完了――下一餐时只要往土豆饼里塞些药……”
“危险的不是那个女人,蠢货!”萨姆尔怒目呵斥,恨铁不成钢地去拧儿子的耳朵,“有问题的是那个骑着陆行鸟的人,施法者们都偏爱禽类坐骑,那家伙很有可能是施法者!”
麦克一愣,随即面露疑惑,“本地的施法者会到咱们家来借宿?外地的……外地来的施法者在咱们赛因没法儿立足吧?”
萨姆尔叹息一声,他有点后悔向儿子吹嘘夸大了自己曾经的冒险经历,养成了儿子不知天高地厚的性格,“没法儿立足,不表示就绝对不会有外地的施法者路过这里。万事就怕万一,万一失手,咱们家就栽了。”
“那到底要不要动手!”麦克反倒是生气了。
萨姆尔怒火上冲,又舍不得揍长子,只好耐心地说道,“他们中有个人吃坏了肚子,明天是走不了的。我们得耐心一些,到了明天,咱们想办法试探一下那个骑陆行鸟的怪人到底是不是施法者。”
萨姆尔父子在灯下低声私语时,窗外,一枚静静躺在泥土之中的、芝麻大小的黑色种子表层散发出一道稀薄黑雾,复又消失不见。
客房中,燃烧着的炭盆前,躺椅之上的安格斯轻轻睁开眼睛。
安格斯有个习惯,如果确认要在某处过夜,他会在不被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往住宿地周边撒上一圈“种子”――将夜袭的埃琳娜等人抽得灰头土脸的亡灵之触,就是“种子”的功劳。
他不信任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同伴。
或者说,明白了智慧生物潜藏于灵魂深处本能的“罪恶”后,任何人都难以再信任他人。
他的“游戏”,或可说是打发时间,也或可说是隔一段时间就必须进行一次的、用以排除精神上巨大压力的解决办法,跟某些国家内部不稳定时不得不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是一样的道理。
缓慢地抬起右手,将手肘支到扶手上,掌心托着下巴,手指在脸颊上轻点。
许久之后,他轻声呢喃了一句,“……接近渣滓的蝼蚁而已,还不够资格。”
必须死的渣滓,才有“资格”接受他的“审判游戏”。可有可无的蝼蚁,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至于衡量“渣滓”与“蝼蚁”的标准……则多数要看安格斯当时的心情。
萨姆尔显然不会想象到他不知不觉间逃过了不止是肉|体上的消亡、连心与灵魂都要被践踏的“游戏”,天色刚明他就吆喝着、斥骂着,把“懒婆娘”和“赔钱货”赶下床做活儿;低眉顺眼的年轻农家女将煮好的麦片、烤好的面包端上桌时,一夜好睡的格洛丽亚抱着个装满甜味香料的罐子兴冲冲地出了房间。
东起来后先看了一遍弟弟,南的脸色好了一些,但仍然全身无力,他就打着哈欠给安格斯端了洗漱的热水后来拿早餐给南;一出门瞧见格洛丽亚又抱出那个让他们吃足“甜头”的罐子,东大惊失色,“女士!等一下!”
“叫嚷什么呢?”格洛丽亚不满回头。
东胆战心惊地看着她手里的罐子,讨好地说,“南还没好转,我给他拿早餐……但是,你知道,南还不太舒服――”
“不舒服的时候就应该吃点儿甜的,你不知道很多地方是把糖当做药品的吗?”格洛丽亚理直气壮。
“或许有些地方是那样的,但我的弟弟我了解,麦片里撒点儿花椒对他更有用,真的。”东摆出百分百真诚的脸色诚恳地说道。
“好吧、好吧。”格洛丽亚悻悻然,她也是好意来着。
端走没被加料的早餐,东跑得飞快。这种畏之如虎的样子让格洛丽亚挺不高兴的,人有了某种偏好的时候总是希望人人跟自己爱好一致,在不做过头的前提下,格洛丽亚也不能免俗。
目光在空荡荡的餐厅里转了一圈,看到退到一边的年轻农家女,格洛丽亚眼睛一亮。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农家女迟疑了好一会儿才以细如蚊蝇的声音回话,“尊贵的……客人,我叫黛茜。”
“你好,黛茜,你喜欢甜食吗?”格洛丽亚笑眯眯地说道。
黛茜眨着迷茫的眼睛看着她。她知道“甜”这个词,但完全没有对于甜味的概念。
多要了一份麦片,格洛丽亚往里面倾倒――没错,就是倾倒――了大量甜味料,往黛茜面前一推,“来,黛茜,尝尝看――这可是东林鲁尔的特产香料,添加了蔗糖粉、奶粉、海带粉、虾粉……又甜又鲜美,回味十足!”
热气腾腾的麦片散发着诱人的香甜味道,战战兢兢的黛茜被这从来没有嗅到的美味诱|惑,即使十分恐惧父亲,也忍不住慢慢靠近她没有资格上的餐桌,哆嗦着伸出手――
“如何,是不是很棒、很有幸福感?”格洛丽亚一脸期待地等着被赞同。
香醇的味道在舌头上花开,暖乎乎的麦片顺着喉管流下;连吃几大口的黛茜使劲儿动着嘴巴,谦卑的、讨好的假笑中浮现发自内心的喜悦……
“死丫头,你在干什么!”从厨房出来的萨姆尔看见这一幕,怒从心起,“快滚开!别弄脏餐桌!”
“对不起、对不起……”黛茜的喜悦转瞬间化为无尽的恐惧惊惶,像被烫到爪子的猫那样猛然弹开、疾步后退,边失措地道歉赔罪、边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
萨姆尔开始大声呵斥女儿,中气十足的嗓门儿和极度侮辱性的词汇让人怀疑他跟这个年轻农家女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被打断兴致的格洛丽亚掏了掏耳朵,她很腻味这种“表演”――眼界不高的家主人总以为在外人面前对自己的孩子非打即骂、耀武扬威很有气势、很有面子,殊不知这样反而往往会让人更加瞧不起他们。
“好了,萨姆尔村长,是我让她试吃我带来的香料的。”格洛丽亚打断了萨姆尔拙劣的表演,看了眼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黛茜,说道,“我想到周边的集市看看,能让黛茜给我带下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