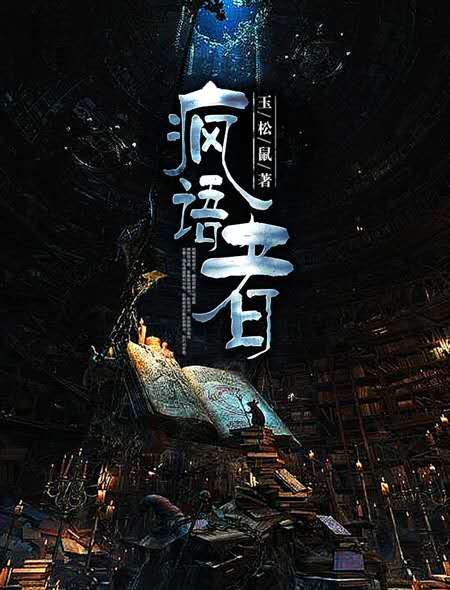我毫不犹豫地上了车,大吼道:“我们走!”
嘭!嘭!
两声响,吓了我一跳。
声音是从后面的车底传来的,我急忙跳下车去看,叶春磊和秦风的车胎爆了。我走过去一看,不知何时,他们车胎下顶着一块锋利的岩石。
我再回到我的车下看,也有一块。我大叫着让所有人下车,检查一下轮胎。蒋云飞的车下也有。
我有些手忙脚乱,将这些岩石通通拔掉。又急忙去帮叶春磊和秦风换轮胎。
身后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听到了鼓声,时而凄厉,时而急促,还有锣声,敲得让人心烦意乱。
牧阳大吼道:“快看那!他们怎么了?”
这一看不要紧,吓得我魂儿都快出来了,那群人足有六十多人,他们浑身是血,如同地狱爬出的恶鬼。有的脸上扎着一根铁叉子,直接刺穿了皮肤;有的在自己背上插着铁钎子,那钎子上还挂着一些刀片;有的刀片直接刺穿了手掌,他高举着手,似乎那是一种荣耀......
后面跟着的人有的端着水果,有的拿着一些饼儿,有的拿着一些黄色、红色粉末,边走边洒。
雾淼淼看着他们,说道:“他们.......是在干嘛?”
“过节吧?”牧阳站在车顶一边拍着一边说道。
这情景我似乎见过,我去过印度,正好赶上乌尔斯节,那一天,异常的血腥,先不说场面,节日后,地面上的血需要三四天才能散去,大个的蚊子就趴在血上,飞都飞不动,现场的血腥味儿让人头皮发麻。
如果你恰好就在节日现场,我建议你准备一个大号的呕吐袋。参加节日的人只要能将自己刺穿的地方统统刺穿。
如果你看到那鞭子,你都会感觉恐惧,因为鞭子的另一头绑着很多刀片,一鞭子抽在自己身上,皮开肉绽;如果你看到锋利的刀子,不用担心会捅到你身上,因为他们会笑着当着你的面,刺在自己身上;如果你看到铁钩子,你会看到有人会将它挂在自己皮肤里,再将自己吊在空中,面带微笑。
我以为这是我人生中见过最恐怖的节日,没想到在泰国的普吉岛,我又一次见到了这个节日,只是相比残忍度,泰国的素食节要比乌尔斯节更加地有视觉冲击。甚至有人将自己的脸颊掏一个洞儿,将蛇穿在上面。
后来,我仔细地研究过这个节日,我以为它只属于某一个民族的特殊节日,但是我错了。我发现不光是泰国和印度,包括伊拉克的“阿舒拉节”,巴基斯坦的自残日......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传统。
我震惊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却有同样的习俗,这是为什么呢?
泰国的素食节,我在当地追寻过本源,说是1825年,传说那个时候有一家很受欢迎的中国戏剧团来到普吉,并在这里停顿下来为矿工们演出。
但是,不久戏团的人就莫名其妙的发起烧来,一个从没见过的人告诉人们,上天说坚信只有严格吃素,祭先帝神明,他们才能康复起来。
于是,连续九个日日夜夜,人们祭拜先祖,只吃素食,远离肉、酒和性。戏团里的人真的很快恢复了健康。
这件事在那里的华人中引起轰动,大家都渴望能更多的了解这个自然康复现象。戏团的演员们将他们奇迹般的快速康复都归结于严格食素以及虔诚的祭拜仪式,并且广而告之。当地人也对此深信不疑。
而我在这几个国家的这种节日中,得到了一个关键词:净化。
终于,我看到了整个仪式背后的意义,每个人身体里都有魔鬼的存在,只有通过痛苦和流血,可以让魔鬼离开,从而有了与神明更加亲近的身体,于是,便要不断地自虐,从而达到心神合一。
而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有人做了驱魔术,并且被民众看到。而这种驱魔术需要将人的身体的不同穴位刺穿,并且施法的这个人活了很久,走了很远,去了很多地方。
言归正传,我一想到那些村民的逃跑,心中更是焦急,可是更换轮胎并不容易,待我们换好,他们已经走到了近前,我听到了笑声和欢呼声。
我看清了他们的穿戴,五颜六色,你很难用语言去形容他们穿的是什么,但他们笑得很自在。
众人也看傻了,我大吼道:“都上车!把车门关起来!我们走!”
我也上了车,我发动了汽车,正准备走,牧阳却说道:“唐老哥,这......他们是不是要给我们吃的?”
我回过头去看,只见两个年轻的女子端着果盘站在我们的车边上,他们的脸上画着古怪的图腾,嘴却用钢钎刺穿封住,那笑显得恐怖且诡异。
而我们前进的方向也堵满了人。
牧阳不知哪根筋儿错乱了,他居然摇下了车窗,将手伸了出去,拿了一个水果。他擦了擦,就要往嘴里塞,我一把打掉,吼道:“你疯了吗?把窗户摇起来!”
牧阳愣愣地看着我,说道:“他们.......没有恶意吧?”
这时,我听到了后面有蒋云飞的声音,他说道:“哦!哦!我不吃的!谢谢!”
我急忙看去,这该死的家伙居然打开车门,下了车。
王雪有些焦急地说道:“唐哥!我害怕!我想走!”
我说道:“别怕!”
而下一刻,我看到了我身后秦风的车上,林黛雨走了下来,她的表情似乎很享受,尽然直挺挺地朝前倒去,接着,被四个男子扛了起来,呼呼喊喊地朝前走。
我大吃一惊,急忙吼道:“你们都不许下车!听到了吗?都不许下车!我去把林黛雨救回来!”
我一步跳下车,冲到了秦风身边,大吼道:“秦风!你怎么把车打开了?”
“我没打开,是林黛雨自己打开的!”秦风吼道。
我简直要背过气去,我大喝道:“走!跟我救人!”
我们下了车,身边的人将我们堵得死死的,他们的钢钎子就在我们眼前晃悠,一不小心就会被扎上。
我大吼道:“林黛雨!你在哪儿?”
没有回应,只有锣的吵闹,鼓点的喧嚣,还有人的欢呼。
但我却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句话,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说汉语。